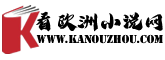第27章 1936年,剑桥(8)
《工人日报》说,从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只有两条路可供游行使用。一条穿过一个叫加德纳角的五路环形交叉口,直达伦敦东区。另一条要经过皇家铸币局街和狭窄的卡布尔街。伦敦塔到斯特普尼区之间还有十几条小巷子,但这些小巷只能并排走一两个人,无法让游行队伍通过。圣乔治街虽然也很宽,但它通往天主教徒聚居的沃平区,不能到达斯特普尼区,法西斯同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
《工人日报》号召人们在加德纳角和卡布尔街树起人墙,阻挡游行队伍。
报纸经常号召人们做一些很难办到的事情,比如说罢工和革命。最近,《工人日报》甚至号召所有左翼党派组织起来形成人民阵线。人墙只不过是它们的另一个幻想而已。需要几千个人才能有效封锁东区,劳埃德不确定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现在两个集结处。
他只知道骚乱不可避免。
桌子边坐着劳埃德的父母伯尼和艾瑟尔、他的妹妹米莉,以及从阿伯罗温过来,穿着正装的莱尼·格里菲斯。莱尼十六岁,是专程来反游行的几个威尔士矿工中的一员。
伯尼把报纸放在一边,抬起头问莱尼:“法西斯分子说你们这些威尔士人来伦敦的车票是犹太大老板买的,有没有这回事?”
莱尼很惊讶,嘴都张成了“O”型。“我不认识什么犹太大老板,”他说,“除非把列维夫人糖果店的列维夫人给算上。她的块头倒真不小。老实跟你们说,我是乘着屠宰场的大卡车,跟送到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的六十头羊一起来伦敦的。”
米莉说:“怪不得你身上这么臭。”
艾瑟尔生气了:“米莉!太没礼貌了。”
莱尼住在劳埃德的卧室里。他向劳埃德承认,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回去。他和戴夫·威廉姆斯将前往西班牙参加镇压法西斯分子暴乱的国际纵队。
“你有护照吗?”劳埃德问。拿到护照并不难,但需要法官、医生、律师或其他有地位的人进行背书,因此年轻人不太容易私下里办上。
“不需要护照就能去,”莱尼说,“去维多利亚火车站搞张周末来回的双程车票就可以了。持有双程车票的人不需要护照。”
劳埃德依稀记得确实有这么回事。这是一项为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商务人士提供的便捷措施,现在却被反法西斯者利用了。“车票要多少钱?”
“三英镑十五先令。”
劳埃德竖起眉毛。一个失业矿工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莱尼告诉他:“独立工党付了我的车票钱,共产党付了戴夫的车票钱。”
他们一定隐瞒了自己的年龄。“你们到巴黎后准备怎么办?”劳埃德问。
“我们在‘巴黎白站’和法国共产党的人会合,”不会法语的他把巴黎北站拼错了,“他们将把我们从那儿护送到西班牙边境。”
劳埃德推迟了自己的出发日期。他告诉别人这样做只是为了让父母宽心,但事实上他是忘不了黛西。他仍然幻想黛西会离开博伊。但希望实在渺茫——黛西从来没回过他的信——可劳埃德就是忘不了她。
此时,英国、法国和美国接纳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提议,同意对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劳埃德对此大为光火:这些民主政府连民选的西班牙政府都不认了吗?更糟的是,正如劳埃德的母亲和比利舅舅秋天在讨论西班牙问题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每天都在打破这项协定。作为英国政府负责相关政策的部长,菲茨赫伯特伯爵却顽固地维护着这项政策,他说不能给西班牙政府武装,否则会有共产化的危险。
正如艾瑟尔在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种自圆其说。只有苏联政府愿意向西班牙提供跨国的帮助,西班牙人无疑会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给予他们帮助的国家感恩戴德。
事实上,英国执政的保守党认为,西班牙选出的都是些危险的左翼分子。如果西班牙政府被极端的右翼分子暴力推翻或是取代,菲茨赫伯特之流肯定乐见其成。劳埃德对此非常沮丧。
现在终于有了在家门口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机会。
“太荒唐了,”伯尼在一周前法西斯同盟宣布游行时说,“伦敦警方必须强迫他们改变路线。他们当然有权游行,但在斯特普尼绝对不行。”警方却说他们对合法注册的游行无能为力。
伯尼、艾瑟尔和伦敦八个区的区长组成代表团,请求英国内政部长约翰·西蒙爵士禁止游行,或至少改变游行的路线,但西蒙爵士同样宣称自己没有这个权力。
工党、犹太人社群和威廉姆斯家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伯尼和其他几个人三个月前成立了犹太人协会,这个协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它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法西斯同盟的游行,不让法西斯分子进入犹太人的街道。犹太人协会提出了西班牙语的口号“坚决不让他们通过”,西班牙政府军在马德里反抗法西斯暴乱时提出的也是这句口号。协会尽管名称响亮,实际规模却非常小。他们在商业大街上租了两个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老式的影印机和几台旧的打字机,但协会在伦敦东区却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短短的四十八小时内,协会就收集到了禁止法西斯同盟游行请愿书的十万个签名。但政府依然置之不理。
议会的主要政党中只有英国共产党支持进行反游行活动,莱尼所属的独立工党也支持这一活动,但独立工党的影响力太过微小了。其他党派对反游行都表示反对。
艾瑟尔说:“《犹太人纪事报》建议它的读者远离街道。”
在劳埃德看来,这正是问题所在。许多人觉得最好远离是非,不要介入矛盾冲突。但这样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
伯尼尽管是个犹太人,但不属于任何教派。他对艾瑟尔说:“为什么跟我提《犹太人纪事报》上的文章?这份报纸反对的是反犹太人的思潮,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谈论他们的观点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说英国犹太人联合会的代表们也持相同的论调,”艾瑟尔说,“显然昨天他们已经在犹太人会堂发表了公告。”
“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代表都是戈德尔格林区的先生太太,”伯尼不屑一顾地说,“他们从没在街上被法西斯流氓袭击过。”
“你是工党的一员,”艾瑟尔带着谴责的口吻说,“工党的政策是不和法西斯在公众场合硬碰硬。你为何要去团结犹太人会众和法西斯斗呢?”
伯尼说:“团结犹太人会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只是在需要犹太人身份的时候才是犹太人,你从来没在街上被人当众侮辱过。”
“但工党也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啊。”
“记住,如果允许法西斯分子挑起冲突,不论是谁起的头,报纸最后一定会怪罪到左派头上。”
莱尼冲动地说:“如果莫斯利的手下胆敢挑起冲突,我们就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艾瑟尔叹了口气。“莱尼,你给我好好想想,是你、劳埃德和工党,还是保守党那边的军人和警察武器多?”
“天杀的!”莱尼愤愤地骂了一句。他显然没想到这一层。
劳埃德愤怒地对母亲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三年前你也在柏林——看到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德国的左派分子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反对法西斯,看看他们遭遇到了什么吧。”
伯尼插话进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没能和共产党组成成员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眼见着共产党人一个个被抓走而没有行动。形成统一战线的话,他们原本有机会赢。”当地工党支部拒绝共产党人的联合要求时,伯尼很是恼火。
艾瑟尔说:“和共产党人联合在一起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她和伯尼在这点上背道而驰。事实上这也是使工党产生裂痕的最主要问题。劳埃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伯尼的支持者。“我们必须用手上能利用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但他马上又宽慰起艾瑟尔来,“妈妈也没错,今天最好不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都留在家,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来反对法西斯主义,那就再好不过了。”艾瑟尔说。
“你希望通过民主政治使妇女得到同工同酬的权利,”劳埃德说,“但是你失败了。”就在去年四月,工党的女性议员提交了一份要求女性劳工与男性劳工同工同酬的议案,但是在以男性为主的下议院没有得到通过。
“不能因为失败一次就怀疑民主。”艾瑟尔干脆地说。
劳埃德很清楚,和德国一样,这种分歧会对反法西斯力量造成致命的打击。今天将是一次严酷的测试。政治党派间可以竞争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权,但谁说了算却是人民群众决定的。他们会听从软弱的工党和《犹太人纪事报》的号召留在家里,还是成群结队地走到街上对法西斯主义说不?到了晚上就能见分晓了。
后门有人敲门,穿着星期天礼拜西装的邻居西恩·多兰走了进来。“礼拜结束后我过来,”他对伯尼说,“我们在哪里集合?”
“两点前在加德纳角见,”伯尼说,“希望有足够多的人在那里阻挡法西斯主义者。”
“东区的码头工人都会去那儿帮你。”西恩热情洋溢地说。
米莉问:“法西斯分子恨的又不是你们,你们出什么头啊?”
“孩子,你太小,你不记得犹太人帮过我们多少忙,”西恩解释,“1912年码头工人起义时,我只有九岁,我爸爸养活不了家人,新市大街面包房的伊萨克夫人就收养了我和我的兄弟们。有她的好心,我们才能活到现在。这样被犹太人家庭收养的码头工人子弟有好几百人。1926年的情形也一样。我们决不允许该死的法西斯涉足我们的街道——莱克维兹夫人,请原谅我的粗鲁。”
劳埃德心头一热。东区有几千名码头工人: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阻挡住法西斯分子就不是问题了。
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响了。“不让莫斯利进入斯特普尼,”一个男人高声大呼,“两点在加德纳角一起集中!”
劳埃德喝了口茶,然后马上站起身。他今天的任务是监视法西斯同盟的行动,确定法西斯分子的方位,并随时通报给伯尼的犹太人协会。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打公用电话用的硬币。“我该走了,”他说,“法西斯同盟的人说不定已经集中了。”
艾瑟尔站起身,跟他走到门口。“别打架,”她说,“别忘了柏林发生的事。”
“我会小心的。”劳埃德说。
艾瑟尔的语气轻松下来。“你要是被人打掉了门牙,那个美国富家千金就不会喜欢你了。”
“她又没喜欢过我。”
“我才不信呢,哪个女孩能抵挡得住你的魅力?”
“妈妈,我没事的,”劳埃德说,“我真的不会有事。”
“我该为你没去该死的西班牙高兴,你说是吗?”
“妈妈,这事今天就别谈了好吗?”吻别了母亲之后,劳埃德就出门了。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温暖得反常。几个人在努特利街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平台,其中一个站在平台上对着扩音器大声喊:“东区的民众们,我们不能任由得寸进尺的反犹主义者欺凌我们!”劳埃德认出演讲者是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在当地的一个代表。因为大萧条,几千个犹太纺织工人失业了。他们每天都会到西特尔街上的劳动力就业中心签到。
劳埃德没走几步,伯尼就追了上来,递给他一包被孩子们称为弹珠的小玻璃球。“我参加过很多次示威游行,”他说,“如果骑警想冲散人群,往马蹄下扔这种玻璃弹珠就可以了。”
劳埃德笑了。他的继父大多数时候是个和事佬,但绝不是什么软蛋。
不过劳埃德不怎么想用玻璃弹珠。他和马匹接触不多,不过它们看上去像是那种隐忍无害的动物,他不喜欢让马匹摔倒在大街上的点子。
伯尼猜出了他的想法:“让马匹摔倒总比人被马踩要好。”
劳埃德把弹珠放进口袋里,但他觉得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一定要用。
他高兴地看到,许多人已经上街了。街上还有许多令他欢欣鼓舞的迹象。墙上到处是用粉笔写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坚决不让他们通过”的标语。共产党出动了很多人,正在沿街分发传单。许多商店橱窗都挂上了红旗。一群参加过上次大战,戴着奖章的老兵打着一面写有“犹太人老兵协会”的旗帜在街上走。法西斯分子想忘了有许多犹太人曾为英国献身,但历史是无法抹去的。其中五个犹太士兵曾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了英国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劳埃德觉得,让这些人参加反法西斯游行,阵仗应该是足够大的了。
加德纳角以苏格兰人开的成衣店——加德纳服装公司得名,是个五条路交会的开阔路口,服装公司的大楼上有个标志性的钟楼。到那里时,劳埃德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此处会起冲突——周围街道上设置了几个急救站,还有数百名穿着制服的急救志愿者。周围的每条小街上也都停着救护车。劳埃德希望最好别出现打斗。但即便有暴力,也比让法西斯分子畅通无阻地游行要好。
为了隐瞒自己的东区人身份,劳埃德绕了个远道,从伦敦塔的西北方向朝伦敦塔行进。还没到那儿,他就听见了铜管乐队的喧嚣声。
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记录了伦敦八百年来的繁荣和衰败。塔旁围绕着一道漆色仿佛被伦敦的经年风雨侵蚀的白墙。墙外背河的一侧是个以伦敦塔命名的公园,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这里集结的。从伦敦塔公园向西到金融区,劳埃德目测已经有几千个法西斯分子集合在了一起。人群中不时爆出有节奏的歌声:
一,二,三,四,
我们要除尽犹太人!
该死的犹太人!该死的犹太人!
我们要把你们斩草除根!
他们打着英国国旗。劳埃德想不通,这些想破坏国家秩序的跳梁小丑,为什么每次活动时都要急不可耐地挥舞象征着国家尊严的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