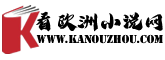第26章 1936年,剑桥(7)
她想起,六月在本·韦斯特安普敦家时,博伊看到她和其他女孩穿男装时一脸激动的样子。那天晚上,博伊第一次亲吻了她。黛西不知道博伊看到她们穿男装为何会如此兴奋——但有些事原本就不可能说清楚。莉齐·韦斯特安普敦说有些男人喜欢女人舔他们下面。这又如何解释呢?
也许应该穿上他的衣服试试。
给他从别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奥尔加对她这么说过。别的女孩多半不会穿男装面对他吧?
她看着衣橱木制衣架上整排的西装、整齐叠放的干净衬衫和打过蜡的黑亮皮鞋。穿上男装会有用吗?时间还来得及吗?
但她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她可以选几件需要的衣服,把它们带到栀子花套间换上,然后赶紧溜回来,希望一路上不会有人看见她……
不能回去,没时间了。博伊的烟马上就要抽完。她必须尽快在这儿换上博伊的衣服——不然就什么都不要做。
黛西下定了决心。
她开始脱裙子。
这下她危险了。在这之前,她都还可以自圆其说,她可以说自己在泰-格温错综复杂的走廊里迷了路,走进了博伊的房间。但在男人的房间里只穿着内衣就说不清楚了,那样只会让她名声扫地。
黛西拿起最上面的那件衬衫,这时她突然想起衣领上要扣一个领扣,她沮丧地叹了口气。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十几个浆白的衬衫衣领和一盒金属扣。她拿起一个衣领,用领扣摁在衬衫上,然后把衬衫套过头。
走廊上传来男人重重的脚步声,她一惊,心头打了一阵鼓,但那人很快就从门前走过去了。
她决定穿一件普通的礼服。礼服的条纹长裤没有背带,不过她在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些。她设法把背带扣在裤子上,然后拉上裤子。博伊的腰足有她两个大。
她把穿着长筒袜的脚踏进黑亮的皮鞋,然后系上鞋带。
她扣上衬衫纽扣,戴上一条银色的领带。领带系得很难看,但这是小事,她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系领带,干脆将错就错。
她穿上一件浅黄色的对襟外套,并在外面套上黑色的燕尾服,然后对着衣橱门内侧的落地镜检视自己的样子。
尽管衣服松松垮垮,但她的样子非常漂亮。
既然还有时间,她索性在衬衫袖子上扣了金袖扣,并在大衣胸袋里放了块白手绢。
好像少了点什么。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少的是什么。
少了顶帽子。
她打开另一个衣橱,在最高的那层架子上发现了一排帽盒。她从帽盒里找到一顶灰色的礼帽,戴在后脑勺上。
这时,她又想起了那天晚饭时造成轰动效应的那几抹胡子。
她没带眉笔。她回到博伊的卧室,趴在壁炉旁边。夏天还没过,壁炉里没有生火。她用指尖沾了点煤灰,回到镜子前,仔仔细细地在上唇处画了根胡须。
她全都准备好了。
黛西坐在一把皮制的扶手椅上等待博伊。
直觉告诉她这样做不会错,但理智上来讲这样做并不符合常规。不过,让他兴奋下也没什么不好。先前博伊带她上飞机就让她兴奋极了,不过他全神贯注驾驶着飞机,不可能在那些狭小的机舱里和她调情。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在天上飞本身已经够让人兴奋的了,博伊想怎么样就任由他去吧。
但男孩是善变的,她害怕博伊会突然动怒。发怒时博伊的漂亮脸蛋会扭曲,会用脚猛跺地板,浑身散发出一股戾气。有一次,在酒吧里,跛腿侍者把他们要的酒送错了,博伊板着脸说:“瘸回你的吧台去,把我点的威士忌拿过来——瘸腿不能成为你眼瞎的理由!”可怜的跛腿侍者被羞辱得脸红了。
如果博伊对黛西出现在他房间感到生气的话,天知道他会说出些什么来。
五分钟后,博伊回到房间。
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来了。黛西意识到自己对博伊已经足够熟悉了。
门开了,博伊走了进来,他并没马上看见黛西。
黛西用深沉的语调问:“老伙计,最近你怎么样?”
博伊吃了一惊。“天哪啊!”又看了一眼以后他才犹犹豫豫地问,“你是黛西吗?”
她站起身。“你猜对了,”她恢复平时的声调说。博伊仍然一脸吃惊地盯着她看。她脱下礼帽,略鞠了一躬,对博伊说:“乐意为您效劳。”接着,重新斜戴上帽子。
过了很久,他才缓过劲,开心地笑了起来。
感谢上帝,黛西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博伊说:“依我看,这顶礼帽真的很适合你。”
黛西走近博伊。“戴上它是为了让你高兴。”
“你真是太贴心了。”
黛西主动抬起头。她喜欢吻他。事实上,大多数男人她都愿意吻。她对自己的这个喜好私下里感到尴尬。在接连几周见不到男生的寄宿制女校里,她甚至连女生都喜欢吻。
他低下头,用嘴唇贴住她的唇。黛西的帽子掉在地上,两人一齐笑了起来。博伊飞快地把舌头伸进黛西口中,黛西放松下来,享受着博伊的舌吻。博伊对所有感官刺激都非常着迷,黛西对他的这种渴望感到非常兴奋。
黛西提醒自己,千万别沉浸在欢愉中,忘了原本的目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博伊如果不求婚一切都没意义了。他难道只满足于简单的一个吻吗?她希望博伊要得更多。以前,时间充裕的时候,他还会把玩她的胸部。
博伊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天中午他喝了多少红酒,他的酒量很好,但一过量性趣就没了。
她把身体贴在博伊身上,博伊趁势把手放在了她的胸前。可黛西穿着宽大的呢绒外衣,博伊一时握不住她的那对小乳房。他沮丧地低吼了一声。
接着他的手掠过她的肚子,伸进了对她过于宽松的裤子。
黛西从来没让博伊如此深入过。
黛西仍然穿着丝质衬裙和棉布内裤,因此他也摸不着多少。他的手却深入到她的大腿内侧,隔着布料紧紧地按住了她那里。黛西兴奋至极。
她把身体缩了回去。
他喘着粗气问:“我越界了吗?”
“关上门。”黛西说。
“天啊,太刺激了。”他走过去反锁上门,然后回来和她抱在一起,博伊重复起刚才未完成的动作来。黛西碰触着博伊的裤子前襟,用力握住他坚硬的下体。博伊快乐地呻吟起来。
黛西再一次抽开身体。
博伊的脸上出现一道阴影。一段伤心的往事浮上黛西心头。有一次,她让一个叫西奥·考夫曼的男孩把手从她胸口拿开。西奥突然翻脸,连声骂她婊子。她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但那次的伤害让她倍感耻辱。此刻,她担心博伊也会这样羞辱她。
博伊非但没有发怒,反而温柔地对她说:“你很清楚,你迷死我了。”
到了做决定的时刻了。进还是退,她问着自己。“我们不应该这样。”她带着没有过分夸大的遗憾说。
“为什么不应该?”
“我们都还没订婚。”
这句话掷地有声。对一个女孩来说,这种话等于变相的求婚。她看着他的脸,害怕他会突然发怒,说出一堆理由,然后让她离开。
博伊却什么话都没说。
“我想让你高兴,”她说,“可是……”
“黛西,我爱你。”他说。
这还远远不够。黛西笑着问他:“真的吗?”
“爱死你了。”
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期盼地看着他。
最后,他终于说出了黛西期待已久的那句话:“你愿意嫁给我吗?”
“哦,当然愿意。”说完她又吻了他。她一边吻,一边解开他的裤带,脱下他的内裤,找到阳具,把它从内裤里拉了出来。那上面的皮肤又软又热,她抚摸着它,想起了和韦斯特安普敦双胞胎姐妹的对话。“你可以揉他的东西。”琳迪说。随后莉齐补充:“揉到它勃起。”黛西对有亲身实践的机会非常兴奋,她喘得更厉害了。
接着,她想起了琳迪的另一句话。“你也可以吸他下面——男人最喜欢这个了。”
她的嘴唇和博伊分开,凑近他的耳朵说:“我可以为丈夫做任何事情。”
说完,她跪了下来。
这是当年最重要的一场婚礼。1936年10月3日,星期六,在威斯敏斯特的玛格丽特教堂,黛西和博伊举行了婚礼。黛西对婚礼不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有点失望,但有人告诉她那里只对皇室成员开放。
可可·香奈儿为她制作了婚纱。萧条期的时尚婚纱线条简单,没有过多的珠宝装饰。黛西的婚纱简单地装饰着蝴蝶边袖口和能被一个花童托起的裙裾。
黛西的父亲列夫·别斯科夫越洋参加女儿的婚礼。奥尔加为体面起见勉强同意在教堂里和列夫坐在一起,假装出幸福亲家的样子。黛西生怕婚礼中玛伽和她与列夫的私生子格雷格会手牵手出现,好在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韦斯特安普敦双胞胎姐妹和梅尔·穆雷是她的伴娘,伊娃是她的主伴娘。博伊对伊娃的一半犹太血统非常介意——他根本没想请伊娃出席他们的婚礼——不过黛西在这点上坚持没松口。
她站在古老的教堂里,心知自己出奇地美艳,欢喜地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在博伊·菲茨赫伯特手中。
她在结婚证书上写下“黛西·菲茨赫伯特,阿伯罗温子爵夫人”这几个字。她为此练了好几周,练完之后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练习纸都撕成了无法阅读的碎片。现在她成为正式的子爵夫人了,“子爵夫人”这个头衔前面写的是她的名字。
菲茨搀扶着奥尔加的手臂亲切地走出教堂,但碧公主和列夫保持着一段距离。
碧公主不是个易于相处的人。她对黛西的母亲非常友好,语气里也许有一丝傲慢,但至少奥尔加没听出来,因此她们的关系还比较和谐。可碧不喜欢列夫。
黛西意识到列夫缺乏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他旁若无人地大声谈笑,用流氓做派抽烟喝酒,根本不去想别人会怎么看。菲茨是个伯爵,因此他可以随性而为。列夫也差不多,他自恃是百万富翁而为所欲为。黛西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在多切斯特宾馆的婚礼早餐会上,看到父亲在英国上层人士面前粗鲁地大声吵嚷时,她还是感到了锥心的疼。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她是阿伯罗温夫人,至少这个头衔是不会被剥夺了。
但碧对列夫的敌意,还是像吵闹声和难闻气味那样让黛西如坐针毡。碧和列夫在主桌旁坐在一起,但碧总是把身体稍稍挪开一点点。两人简单交谈时,碧也没正眼瞧过他。列夫似乎没注意到碧的不恭,仍然笑着畅饮香槟,但坐在列夫另一边的黛西知道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列夫的确有点粗野,但绝不愚蠢。
酒酣耳热,男人们一边抽烟一边交谈。新娘的父亲列夫依例为这顿饭付了账单。他看着桌子那头的菲茨赫伯特伯爵,问:“菲茨,希望你喜欢这顿饭。这几瓶红酒还合你的胃口吗?”
“很好,谢谢你。”
“没错,真他妈的是好酒。”
碧大声咂舌。在她看来,上等人不该说“他妈的”。
列夫转身看着她。他笑盈盈的,但黛西从他眼中读出了危险的信号。“公主,为什么这样?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碧公主没有答话,但列夫充满期待地看着她,目不转睛。最终她开口了:“我不想听脏话。”
列夫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没有立即点燃,而是闻了闻烟味,拿在手里把玩。“我讲个故事吧,”他扫视桌边众人,确认菲茨、奥尔加、博伊、黛西和碧都在听他讲话,“小时候,我父亲因为在别人的土地上放牧而被起诉。你们也许会想,即便他真的有罪,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他被捕后,地主在北面的草地上立了个大十字架。之后,沙俄士兵到了我家,把我、哥哥和我们的母亲带到草地上。到了那儿,我们就看见父亲被吊在十字架上,脖子里缠着绳圈。没多久,地主来了。”
黛西没听说过这件事。她把目光投向了母亲。奥尔加看上去也很吃惊。
桌子旁的一小群人都不再说话了。
“我们被迫旁观了父亲被吊死的全过程,”说到这里,他转身看着碧。“这里有一点很奇怪,地主的妹妹竟然也在那里。”他把烟叼在嘴里,口水沾湿了烟的过滤嘴,但他马上又把烟从嘴边拿开。
黛西发现碧脸色煞白,这是在说她的事情吗?
“地主的妹妹是个公主,当年她十九岁。”列夫看着手里的烟。黛西听到碧惊呼一声,这才意识到父亲说的这位公主正是自己的婆婆。“她冷冷地看着我父亲被绞死,就那样站着,动都没动。”列夫说。
接着,他直直地盯着碧,说:“在我看来,这才是所谓的粗野。”
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列夫把烟放回嘴边说:“谁有火啊?”
劳埃德·威廉姆斯坐在阿尔德盖特母亲家厨房桌子旁,仔细地审视着一张地图。
这天是1936年10月4日,星期天,伦敦将发生一场骚乱。
伦敦城区泰晤士河畔依山而建的罗马式老城区现在成了金融区。小山西面是富人家的住宅,以及他们趋之若鹜的剧院、商店和教堂。劳埃德的母亲家在山的东面,毗邻码头和贫民窟。一直以来,移民们在这里的码头登陆后辛苦劳作,只希望他们的后代有朝一日能从伦敦的东区搬到西区。
劳埃德专心致志看着的是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号外上刊登的地图,上面标出了英国法西斯同盟这天的游行行进路线。他们计划集结在城区和东区交界的伦敦塔下,然后向东行进——目标直指主要居住着犹太人的斯特普尼区。
除非劳埃德和他的同伴能制止他们。
报纸上提到,伦敦有三十三万犹太人,其中有半数居住在伦敦东区。他们大多是来自苏联、波兰和德国的难民,害怕有朝一日警察、军人或哥萨克人会闯入他们的家园,抢劫财产,鞭打老人侮辱妇女,把他们连同儿孙一起拉到墙边枪毙。
在伦敦的贫民窟里,这些犹太人找到了能让他们享有和普通公民同等权益的地方。如果他们望出窗外,看到一伙穿着制服的流氓在犹太人住的街道上发誓要扫除犹太人,又会怎么想呢?劳埃德觉得真的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