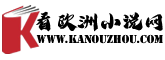魂旦,旦角里那么特殊的一个行当。她们通常穿着白色有水袖的褶子,或长帔,幽艳而诡媚,踮起脚尖,踏着碎步,捏细嗓子,拖长声音喊一句:“冤——啊——”让人连脊背都凉了。
是旦角,所以都漂亮,年轻,有着万千心事,一缕幽情,娇怯怯灵魂无主,我见犹怜,由不得不听她细细道来一腔委屈。
《牡丹亭·冥判》里的判官,那样刚硬威直,见了杜丽娘的魂儿也惊艳,赞叹说:“猛见了荡地惊天女俊才,血盆中叫苦观自在。”
丑扮的小鬼提议说不如收作后房夫人,判官喝骂:“嘟,有天条擅用囚妇者斩。则你那小鬼头胡乱筛,俺判官头何处买?”——显然也是愿意的,只是不敢。
患得患失,欲近还远,这与凡间男女见了心上人的矛盾心情有何异?
为了这份怜香惜玉情怀,判官不厌其烦地查了鬼簿又询问花神,最后许杜丽娘“随风游戏”,尸身不朽,好等那秀才柳梦梅来掘坟成亲。
好一个多情的判官!
阳光斜斜地照进剧团的服装间。
小宛倾箱倒箧,按照封条开启所有的梅英衣箱。《牡丹亭》、《西厢记》、《风筝误》……箱子足有五六口之多,收藏颇丰。小宛一一打开,将绫罗绸缎挂了满架,徘徊其间,仿佛走在一座没有日照的花园里。
名伶的行头本身已经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折子戏。
当那些衣箱打开,旧时代的色彩便水一样从衣裳的褶层里,从水袖底下,从绣线的缝隙流泄而出,像关掉了音响的色情电影,在没有月光的暗夜里独自妖娆。
服装的性感,是无可言喻的,亲昵,然而矜持。
小宛是学服装设计的,深深知道嗜衣的人多半都有强烈的自恋倾向。若梅英,是其中犹甚者吧?
这是戏衣的世界,灵魂的园林,充满着若梅英的气息。
戏衣之于若梅英,就像月光之于月亮,花香之于花朵,蝉壳之于蝉,鱼鳞之于鱼。
阅读衣裳,就是阅读若梅英。即使隔着六十年的风霜烟尘,依然可以从这些沉香迷艳里揣想主人的风致。
那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她一直活到三十多岁,可是在小宛的心目中,却只看见二八年华的她,在北京城,在上海滩,在戏台上,在菊宴间,她的眼风笑痕纠缠在风花雪月里,千丝万缕地缠绵着,不可分割。
一个唱京戏的女子,与唱流行歌曲的周璇、阮玲玉等大概是没有什么相似的吧?她们的共通之处,只是生活在一个时代,并且,都是名伶。
但在那时的人的眼中,伶人与歌星的地位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十伶九妓,歌星,却是有手腕的交际花,是《日出》里的陈白露,戏子,最多是陈白露搭救的小东西,任人玩弄,而没有游戏命运的资本。
若梅英,是被命运所戏,还是戏弄了命运?
戏子属于舞台。走在台下芸芸众生中的若梅英是无法想象的。老北京的戏子从小被班头打骂惯了,规矩严,功课重,难得出趟门儿,就好像林黛玉进荣国府,不敢多行一步路,不肯多说一句话,“生怕被人耻笑了去”。要是换作上海歌星,怕人笑?她不笑人就敢情好了。
若梅英的一生,不知有没有真正地任性过?
认真地讲,她并不只属于三四十年代,她一直活到了“文革”,生命远比旧上海的金嗓子们真实得多也风尘得多。
然而所有死去的人的记忆,不论远近,都属故事;如果故事的真相被湮没被遮盖,有了不同版本,就成了传奇。
小宛想象着若梅英扭扭捏捏地穿着荷叶边的改良旗袍的样子,大概远不如上海歌星的潇洒惬意,而多半是有些局促的。至于解放后全民一致的灰蓝褂子,就更加无法想象如何与若梅英联系在一起了。属于梅英的,只有戏衣,越华美越不切实际的戏装,才衬得梅英越鲜活明丽。
小宛将一件明黄双缎绒绣团凤的女皇帔披在身上,触摸着绣线绵软的质感,心绪温柔。
鬼魂是虚无缥缈而令人心生恐惧的,故衣却亲切真实,是具象的历史,有生命的文字。那层叠的皱褶里,长帔的裙摆里,处处藏着性情的音符,怀旧的色彩,一种可触摸的温存,仿佛故人气息犹在,留恋依依。
戏衣连接了幽明两界,沟通了她和若梅英。
门外传来唱曲声,是演员在排新戏《倩女离魂》,正练习张倩女抱病思王生、忽然接到报喜佳帖一折:
“将往事从头思忆,百年情只落得一口长吁气。为甚么把婚聘礼不曾提?恐少年堕落了春闱。想当日在竹边书舍,柳外离亭,有多少徘徊意。争奈匆匆去急,再不见音容潇洒,空留下这词翰清奇。把巫山错认做望夫石,将小简帖联做断肠集。恰微雨初阴,早皓月穿窗,使行云易飞……”
因是新戏,演员唱得略觉凝滞,有气无力的一种味道,倒也与曲意暗合。
想那张倩女,一边厢自己的魂离肉身,去追赶王生成双成对去了;另边厢肉身抱病,还在念着王生恨着王生的负心。却不知,自己的情敌,原来是另一个自己。
一本糊涂帐。
或者,这算不算是高度夸张了的精神分裂?
小宛一边听曲,一边抚弄衣裳,蓦然间,手上触到了什么,硬硬的——原来,是帔的夹层里藏着一枚绒花,一封拜帖。
帖子绢纸洒金,龙飞凤舞地写着:“英妹笑簪:愿如此花,长相厮伴。朝天。”
朝天!张朝天!
这个张朝天果然不简单,他绝不仅仅是个吹捧若梅英写“鳝稿”的小报记者,而更应该是她的心上人!否则,以梅英的清高自许,绫罗珠宝亦都弃如草芥的,怎会将个不相干男人的赠品收藏在自己最珍爱的戏装衣箱里?而且,连青儿都瞒过。
只是,她与张朝天之间,到底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又为何劳燕分飞,钗折镜碎了呢?
那一枚精致的绒花让小宛觉得亲切,仿佛忽然间按准了时间的脉搏,瞬间飞回遥远的四十年代。
要这样实在的物事才让人感动,要这样细微的关怀才最沁人肺腑。透过古镜初磨,她仿佛清楚地看见戏院的后台,那风光无限的所在,张朝天将一枚绒花轻轻簪在梅英的发际,两人在镜中相视而笑。镜子记下了曾经的温柔,可是岁月把它们抹煞了,男婚女嫁,各行天涯,一点痕迹都不留下。
不,有留下的,总有一些记忆是会留下的,就好比这枚绒花。
小宛对着镜子把它插在自己的发角,对着镜子端详着。忽然,她愣愣地望着镜子,只觉身子僵硬,一动也不敢动。那镜子里,自己的身后,还有一个人,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套自己刚刚挂到架上的通身绣立领大襟的清代旗装,梳偏凤头,插着金步摇,是《四郎探母》里铁镜公主的妆扮,气度高华,而身形怯弱,正忧伤而专注地看着自己,似乎不知道该不该上前招呼。
小宛屏住呼吸,半晌轻轻说:“你来了?”
女子在镜中点头,欲语还休。
小宛缓缓转过身来,便同她正面相对了。看清楚了,反而松下一口气,不觉得那么可怕——只为,那女子真是美,美得可以让人忘记她不是人,而是一只屈死的鬼。
女鬼依恋地望着小宛身上的皇帔,脸容寂寂,半晌,幽幽地说:“这一件,是我刚上戏时,唱青衣,在《长坂坡》里扮糜夫人,戏里有‘抓帔’一场,就是这件帔。”
抓帔?小宛只觉头皮一紧,大惊失色。“抓帔”是戏行术语。《长坂坡》里,糜夫人路遇赵云,将怀中阿斗托孤后,投井自尽,赵云赶上一抓,人没救下来,只抓到一件衣裳——戏里戏外,这件帔的意义竟然都是“死”。
“对不起,对不起。”小宛将彩帔急急扯下:“我不是存心要穿你的衣裳。”
女鬼恍若未闻,又走向另一件云肩小立领的满绣宫装,低声回忆:“这一件,是民国三十四年,我已经成了角儿,在中国大戏院,唱《长生殿》……”
民国三十四年?小宛忍不住在心里默默计算那到底是公元哪一年。却见若梅英已经又指向旁边一件黄地团花回纹龙凤呈祥的宫装:“这件,是《彩楼配》里王宝钏出场时的行头,那时候王宝钏还是相府千金,身份尊贵……”
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那时候王宝钏还是相府千金,身份尊贵,衣裳也华丽无比。但她在彩楼之上,抛绣球打中了薛平贵,从此荆钗布裙,洗尽铅华,苦守寒窑十八载,用半生沧桑换得一个虚名儿后人钦敬。
值得?不值得?
随着若梅英的没有重量的行走,两架的衣裳都一齐微微摇摆,无风自动,似乎欢迎旧主人。
戏里,戏外,一件件,一出出,都是故事。
小宛忽然想,“依依不舍”的“依”字是一个“人”加上一件“衣”服,是不是说,所谓“依恋”的感觉,就好比一个“人”对于一件“衣”的温存。
旧衣裳就像老房子,是有记忆的,曾经与它们的主人肌肤相亲,荣辱与共,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事可以比衣裳更亲近一个人?衣裳伴着它们的主人一同在舞台上扮演某个角色,经历某个春天。洒满那么多或倾慕或艳羡或妒恨或贪婪的目光,承接过那么响亮热情身不由己的掌声,这一切,人没有忘,衣服又怎会忘?
“这一件,是民国三十六年,唱《游园惊梦》……”梅英在一件“枝子花”兰草蝴蝶的对称纹样女花帔前停住,轻轻说,“那天在电影院里,我唱《游园惊梦》,想把你带到那个时代去叙一叙,但是你很怕。”
小宛有些害羞,勉强笑笑:“现在不太怕了。”
若梅英抚摸着花帔上的绣样,神情怅惘:“《游园惊梦》的故事真好,那个翠花,也唱过戏,也抽鸦片,也做了人家的姨太太,真像我……可是她有容兰做伴,还有二管家……比我好命多了。”她忽然又抬起头来,专注地望住小宛:“我是鬼,你真的不怕?”
“你会不会害我?”小宛反问。
“不会。”若梅英肯定地回答,“我在人间,只有你一个朋友。”
“你不会害我,我当然就不怕你了。”朋友两个字叫小宛觉得窝心,这次她是真地微笑了,“不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呢?”
“我也不知道……”若梅英沉吟,忽然问,“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12月18号。”
“今年23岁?”
“其实是22。”小宛纠正,但接着反应过来,老辈人算的是农历,逢年加一岁,不禁问,“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梅英苦笑,“如果我活着,今年该是83岁。”
“大我60年。”
“刚好一个甲子。从佛历上讲,也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你和我,八字完全相合,所以容易沟通。”
“可是,和我同生日的人多着呢。全世界同一天同一分钟出生的人不知几千几百,你为什么不找他们?”
“并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的。”梅英轻叹,“你忘了?那天是七月十四,鬼节,我们放假三天,可以到阳间走一走,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忽然你开了衣箱,我糊里糊涂地,就上来了,第一个碰到的人就是你……”
若梅英有些抱歉地望着她:“除了你,我并不认识别的人。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找不到,我是个鬼,没什么能力,只得托付你……”
“谁?你要找谁?”
“他姓张,是个记者。”
“啊?谁?”小宛心一阵狂跳,“之乎者也”的名字已经跳到嘴边来。
然而若梅英说:“他叫张朝天。”
“哦是。”小宛定下神来,脸上犹自羞红难褪。当然是张朝天,自己想到哪里去了?
只听梅英幽幽地道:“我找他,只想问他一句话。”
“什么话?”
“我要问他一句话。”梅英凄苦地望着满架戏衣,自言自语,“世间三十年为一劫,在阳间的人,讲究三十而立,如果到了三十岁还不能立业立家,也就一生蹉跎;在阴间的鬼,则是三十年一轮回,如果三十年后还不肯投胎转世,就错过缘头,再没有还阳的机会了。我在这三十年间,缥缥缈缈,游游荡荡,只为了要找到张朝天,问他一句明白话。可是,三十年过去,我始终没有他的音讯,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我几次都想放弃,可是这一段情一盘债无论如何放不下。我错过了投胎的最后时限,已经再也没有投胎的机会了,唯一要做的,只是等待一年一度的七月十四,好上阳间来找他。那天,我随着一干尚未还阳的鬼来到人世,迷迷糊糊地在街道上走着,没有方向,不能自主,可是忽然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让我若有所动,就身不由己地随了来,进了一处院落,正看到你在那儿试衣裳……”
“换句话说,就是离魂衣给你引了路,并且把你留在阳间了?”
“是的。做鬼魂的,没有自己的力量和形式,必得有所凭藉才能存在。要么附在某个人身上,要么附在某件东西上,我的魂儿,就在那些衣冠钗带之中了。”
小宛看着身着戏衣的若梅英,心中怆恻,忽然想起一事:“你说你们放假三天,可是现在早已过了期限,你为什么还会留在人间?”
“我回不去了。”梅英幽幽地叹息,“我难得遇到你。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如果这次我再不能找到他,就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到他了。所以,到了三天期满,我仍没有走,藏在衣箱里躲过鬼卒判官,宁可留在人间做个孤魂野鬼,也不要再回去。”
三天,就是七月十七,也就是胡伯死的那天。难道,是若梅英利用胡伯来与鬼卒做交易,李代桃僵?真不知道自己一番奇遇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她帮助一只鬼来到阳间,找寻她生前的一段孽缘疑案,却因此而害了胡伯的性命。也可以说,是她的行为间接杀人,她,才是那个幕后的凶手。
凶手?小宛打了一个寒颤:“你留下来,就是要我帮你找张朝天?”
“我为他跳楼,为他变成游魂野鬼,就是想问他一句话。四十七年了,我每年鬼节都会上来找他,可是一直找不到。为了他,我怎么都不肯去投胎,不肯喝孟婆汤,不肯过奈何桥。我不想忘。我要记着,要问他一句话。”
“他,和你到底有什么恩怨?”小宛怯怯地问,一边害怕,一边忍不住好奇。是什么样的情仇冤孽,可以使一个人坠楼自尽,又可以使一只鬼拒绝投胎,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纠缠,誓要问他一句话。
我要问他一句话。什么话呢?
梅英幽幽地回忆着:“我是在上海唱戏时认识的他。他是申报记者,常来看我的戏,每次看完了回去都会写文章赞我,他的文章写得真好,词儿好,意思也好,我也不是很懂,可是只觉得,他的文章和别人不一样,句句都能说到我心里去。”
小宛着迷地看着若梅英忽嗔忽喜,忽行忽坐,只觉她怎么样都美,美得惊人。她说,如果她还活着,该有79岁,那应该是个鸡皮鹤发的老人了,或许,就像胡瘸子那样,老成一截枯枝,一页黄历。可是,既然做了鬼,岁月从此与她无关,她永远地“活”在了自己最喜欢的某个年代,极盛的时候,风光的时候,初恋的时候——当她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那种妒煞桃李的娇羞就更加婉媚可人。
“在他以前,我也见过许多人,年轻的,老的,有钱的,有权的,他们对我献殷勤,送花送头面,请吃请堂会,我都不在意。不过是应酬罢了,没什么真心……可是自从遇见他,遇见他……”
梅英的声音低下去,低下去,不胜娇羞。小宛入迷地看着她,只觉她每一举手一投足,都美不胜收,而那一种京戏名旦所特有的柔媚声线,更是一直钻进人的心里去。
“他哦,和别人都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我也说不来。可是,我看到他就会心跳,脸会红,会烫,总觉得有什么好事儿要发生;看不见他,就会想念,牵肠挂肚,做什么都不起劲儿。我再也不喜欢去北京唱,想方设法留在上海,就为了他在上海……”梅英忽然转过头来,看着小宛,“你,爱过吗?”
小宛吃了一惊,爱过吗?自己正在恋爱,同张之也。可是,他已经三四天没露面了,只通过几次电话,口气冷淡得很。她真是有些害怕,怕阿陶忽然失踪的一幕会重演。为什么,自己的每次爱情故事都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即濒临结束?难道,这是命运?
“你有没有试过很深地爱上一个人,痛苦地爱着一个人?”梅英幽幽地问,可是并不等她答案,只顾自说下去:“我爱上他。从我知道自己爱他以后,就再也不肯接受别的男人的约会,也不去应酬客人,只一心一意等着他向我表白……我天天买他的报纸来看,看到他的名字就喜欢。每天上戏前都要看他有没有来,一边唱戏一边偷偷地看他,他常坐的那个位子,他总是在的。”
梅英的神情越来越温柔,细语悄声,历数六十年前风月,仿佛只在昨天:“那时的戏院分三层楼,三楼的座位是卖给那些劳苦人的,拉车的,扛活的,坐得高,也远,看不仔细,可是他们叫好的时候喊得最起劲儿,有他们在,就不怕冷场。所以我们每次上场前,都在台幕后面掀起一角来望望三楼,要是那里黑鸦鸦坐满了人,就心里有底了。可是,自从‘他’之后,我就谁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楼下的达官贵人,也看不见楼上喊好叫彩的,就只看见他一个。他总是穿长衫,戴一顶礼帽,看戏的时候就把帽子拿在手里,总是正襟危坐,看完戏就走,从不主动到后台来搭讪,写了稿子也不向我卖人情。可越是这样,我越喜欢。他在,我就会唱得很起劲儿,眼风姿势都活络……”
一句一个“他”,不点名不道姓,却声声都是呼唤,字字都是心意。
小宛崇古情结发作,望着若梅英,满眼都是艳羡,痴痴地问:“你们约会吗?跳舞吗?有没有去外滩坐马车?他给你的情书,是写在什么样的信纸上?要不要在信封里夹着花瓣,或者洒香水?”
“要的。”梅英微微笑,妩媚地将手在眼前轻轻一挥,仿佛自嘲,“不过不是他,是我。我每次给他写信都用尽心思。我识得的字不多,写每封信都要花好大力气,不认得的字,要去问人。不敢问同一个人,怕被人拆穿。要分开问,问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里,这样子,写一封信往往要用上三五天。写完了,就对着镜子细细地涂口红,再印在信纸上,算作签名。没有洒香水,怕盖住了胭脂的味道。花瓣是粘在口红上的,这样子才不会花掉。收信的人,揭开花瓣,会看到一个完整的唇……”
那样缠绵旖旎的情爱哦。小宛悠然神往,完全忘记自己是在与一只鬼对话,注意力完全集体中在情书上。
情书?这在今天早已经是失传了的游戏。现代人,发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还要错字连篇,狗屁不通。他们会为了一个不识的字花尽心思去问人吗?字典在手边都懒得翻一下呢。
“他回你的信吗?”
“没有。一次都没回过。”
“这么忍心?”小宛有些意外,这样一个可人儿的情意,什么人可以抗拒?一个可以洋洋洒洒写宣传稿的记者,为什么却要吝啬写一封信?
“他不是忍心,是诚心。因为他说,写字是他的工作,再好的文字也不能表达他的心意。再说,他对我的赞美,都已经登在报上,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还有什么要写的呢?”梅英袒护地分辩,口吻里满是溺爱,“他虽然不回我的信,可是他曾经送我一只珠花,就是你现在戴的这枚。”
珠花?小宛尴尬地笑,赶紧把珠花摘下来还给若梅英。一次又一次不告自取,穿了人家的衣裳,戴了人家的花,又怎能怪她不上来找她?
若梅英接过珠花,温柔地打量,仿佛在重温那些永远想不够的往事。“我爱他,偷偷地、大胆地爱着,一次次暗示,一次次邀约,他总是推脱。可便是那样,现在想来也是开心的,因为有希望。他来看我的戏,尽管不应我,可是夜夜来看我的戏。于是我知道,他也是喜欢我的。可是他拒绝和我私下里见面。越是这样,我越是放他不下。睡里梦里都想着他。想着他,就觉得好开心。被拒绝了也是开心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太阳每一天升起来都有非凡的意义。都充满等待和希望。世界是因为有了他才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日子,足足过了半年。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应了我。”
“他应了?”小宛忍不住欢呼起来。这样的痴情,在今天早已绝迹,使她在梅英的叙述中总捏着一把汗,生怕是个始终没有高潮的单相思故事,那样也未免太叫人不甘。知道那铁石人终于也有心动的时候,她忍不住代她兴奋,觉得喜欢。而且,她有一种奇怪的联想,总觉得自己和梅英的命运在冥冥中紧密相连,如果她的爱情可以得到回应,那么,自己也可以。
“他应了?你们相爱了?”
“是的,我们相爱,他清楚地告诉我,他也是喜欢我。他还送了我珠花,写了字条。他为我写过那么多文章,都变了铅字登在报上,可是那张字条,却是我拥有的他惟一的亲笔字。”梅英幽幽地说,那样柔媚缠绵的一段往事,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的声音里却殊无喜悦,而暗含着一股阴森的冷意,让小宛不寒而栗。
“那段日子,我被一个广东军官纠缠,已经发下话来,说再不答应就要抢人的。我求他想办法,求他带我走。他答应了。我们约好要在七月十三那天晚上偷偷成亲,然后私奔。我们约好了的。我在酒店开了房间等他。布置了新房,买了新被褥,我亲手绣的花,一针一线,刚学,绣得不好,可我绣得很认真,绣了很久,手上不知扎了多少针……”
梅英停下来,捧着自己的手,仿佛在寻找曾经被绣花针扎伤的针眼。绣的心情是甜蜜的,那些刺伤却是疼痛的,指尖的血滴在绣被上,被彩线遮掩了。那到底是一床甜蜜的鸳鸯被,还是疼痛的血泪裀?
小宛有些栗栗地问:“后来呢?”
当她这样问的时候,心里已经隐约猜到了答案,然而若梅英亲口说出的时候,她还是觉得震惊而伤心。
“我等他,等了整整一夜,可是,他竟没有来!”梅英的声音变得凄厉,“我要问他,问他为什么负我。我不肯忘记,做鬼也不愿意忘记,我要问他一句话,我那么爱他,信他,等他,可是他没来。他竟没有来。他负我!他负我!他负我!”
她看着天空,忽然发作起来,长发飞起,像受伤的兽一样嘶声哀号。
是时风沙突起,拍得窗棂栗然作响,小宛忍不住双手捂住耳朵,惊怖地呻吟出声。怎样的弃约背义,竟令一个女子如此耿耿于怀六十年,死不瞑目,即使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
这强烈的感情叫小宛颤栗起来,几乎不能相信这故事的残酷。
当她再放下双手时,若梅英已经不见了。
那惨痛的往事回忆刺激了她,即使已经隔了六十年,即使她已经变成一只鬼,仍然不肯忘记曾经的痛楚与仇恨。
门外女演员还在唱着:
“都做了一春鱼雁无消息……魂逐东风吹不回……”
满室华衣间,小宛流满一脸的泪,却不再是因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