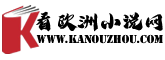第36章 1939年,柏林(1)
托马斯·马赫看着沃洛佳·别斯科夫走出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六年前,德国秘密警察转型为更有效率的新型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但马赫支队长依然掌管监视柏林的叛徒和破坏分子的部门。最危险的破坏分子无疑要接受菩提树下大街63-65号——苏联大使馆的指令,因此马赫和手下时刻监视着从那里进出的人。
苏联大使馆是一幢白色大石建成的城堡。八月的阳光照射在建筑的石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使馆中间的屋子前竖着一根巨大的灯柱,两侧的廊道上开着几扇像站岗哨兵一样的落地窗。
马赫坐在大使馆对面人行道上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最优雅的大马路上车水马龙;女人们穿着最漂亮的裙子在商店里购物,男人们穿着西装和制服在街道上来来往往。很难相信这样的德国还会有共产主义者。怎么还会有人反对纳粹呢?德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消灭了失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起义和罢工已经成为过去坎坷岁月的久远回忆。警察可以严肃高效地扫除罪恶。德国正在加速发展:许多家庭都有了收音机,不久之后老百姓的私家车就能奔驰在新造的高速公路上了。
这还不算什么。在经历了上次大战后的萎靡不振以后,德国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军队武器精良,军力强大。过去两年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被并入了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德国签订了《钢铁条约》,借此和德国联起手来。这一年早些时候,马德里最终落入了佛朗哥的叛军之手,西班牙成立了一个亲法西斯的政府。德国人怎么会无视这些成果,把国家送入布尔什维克之手呢?
在马赫眼里,这些人是垃圾,是害虫,必须找出来全部肃清。一想到这些人,马赫的脸就气得扭曲变形。他用脚狠跺着人行道,像是想踏死一个共党分子似的。
这时他看见了别斯科夫。
马赫看见的这个年轻人穿着蓝色的华达呢大衣,胳膊上挂着似乎为换季准备的薄外套。尽管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但几乎剃光的头发和飞快的步速却说明这是个军人。从他随意却完整地观察街道的姿态来看,这个人不是红军情报机关的特工就是苏联内务部的秘密警察。
马赫心跳加快,他和手下认得出大使馆里的每一个人。盖世太保的文件上有苏联使馆所有人员的护照照片,他们每天都要看上几遍。但马赫对别斯科夫知之不多。别斯科夫非常年轻——马赫记得文件上记录的是二十五岁——多半是个无足轻重的低级别外交官。不然,他就是故意让自己显得普普通通。
别斯科夫穿过菩提树下大街,朝马赫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和弗里德里希街的拐角处走了过来。马赫发现走近的苏联人非常高,有着运动员的身材。他的目光锐利,眼神机警。
马赫移开视线,突然间非常紧张。他拿起杯子,喝了口冷咖啡,用杯子挡住自己的半边脸。他不想直面那双蓝色的眼睛。
别斯科夫拐进弗里德里希街。马赫向站在对面街角的莱因霍尔德·瓦格纳点头示意,让瓦格纳跟上别斯科夫,然后他从桌旁站起来,跟上了瓦格纳。
红军情报机关的雇员不一定都是间谍。他们取得的信息大多数是从合法渠道得来的,比如说看报纸。他们不需要什么都信,只需记下诸如哪个军工厂又招聘了十个熟练的机床工这类细节。另外,苏联人可以在德国各地旅行——苏联则不然,没有苏联特工的陪同,任何国家的外交官都别想离开莫斯科一步。马赫和瓦格纳追踪的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是个从报纸上收集信息的情报人员——只要能掌握熟练的德语,具有一定的总结能力,任何人都能从事这份工作。
他们跟着别斯科夫走过了马赫弟弟开的饭店,那里仍叫罗伯特酒馆,但顾客群完全变了。罗伯特酒馆原来招待的是有钱的同性恋者、犹太商人和他们的情人,以及那些能挣钱也能喝酒的女演员。现在这些人不是被送进了集中营,就是躲起来不敢露面。一些人干脆离开了德国——赶他们出去非常好,马赫想,即便酒馆不能像以前那么赚钱,他也不愿意和这类人呼吸一样的空气。
他想到酒馆原先的主人罗伯特·冯·乌尔里希,他依稀记得罗伯特去了英国,也许在英国又开了家为同性恋服务的餐馆吧。
别斯科夫走进一个酒吧。
一两分钟后,瓦格纳也进了酒吧,马赫在酒吧外负责监视。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酒吧。等待别斯科夫重新现身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士兵和他的恋人、两个穿着考究的妇女和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出这间酒吧。接着瓦格纳出来了,他直视着马赫,双手一摊做了个迷惑不解的手势。
马赫穿过街道。瓦格纳非常丧气:“他不在酒吧里。”
“你全部都看过了吗?”
“是的,连厨房和厕所都看了。”
“你问过酒吧里有谁看见他从后门出去了吗?”
“他们说没看见。”
马赫害怕极了。这是全新的德国,出点小错不是能轻易糊弄过去的,他也许将遭到严厉的处罚。
但这次应该没事。“很好,就这样吧。”他说。
瓦格纳显然松了口气:“真的吗?”
“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马赫说,“从摆脱我们的熟练程度看,这家伙是个间谍——而且是非常优秀的间谍。”
沃洛佳进入弗里德里希车站,坐上地铁。他脱下让他看起来像个老头的帽子、眼镜和脏雨衣。他坐下来,拿出手绢,擦掉使鞋子显得脏污的粉末。
他有点担心那件雨衣。这是个大晴天,他害怕盖世太保注意到它,意识到他的换装。不过盖世太保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聪明,自从在酒吧厕所快速换装离开以后就没人跟着他了。
他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被人看见他和德国持不同政见者联系,最好的结果是事业失败被遣送回苏联。运气差一点的话,他和联系人可能会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16]的地堡里销声匿迹。苏联人会对外交官的失踪进行抗议,德国人会装模作样地进行失踪人员的搜索,最后遗憾地报告说没有结果。
沃洛佳自然没去过盖世太保的总部,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列森伯格街11号的苏联贸易大厦建有相同的设施:钢门,用便于清洗血迹的方砖建成的审讯室,一个便于分割尸体的大盆,以及焚烧人体的电炉。
沃洛佳被派到柏林的任务是扩展这里的间谍网。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了胜利,德国对苏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斯大林撤了外交部长利特维诺夫的职,让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坐上了外交部长之位。但莫洛托夫又能做些什么呢?法西斯势力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欧洲蔓延。在一战中,德国军队战胜了苏联的六百万大军,这样的回忆让苏联高层寝食难安。斯大林想和英法签订一项抑制德国的条约,但三国无法达成一致,这份条约在最后一刻流产了。
德国和苏联这场仗迟早要打,沃洛佳的任务就是为苏联打赢这场仗而收集尽可能多的军事情报。
他在柏林市中心以北贫苦的工人区维丁下了地铁。他在站外停住脚步,假装读墙上的海报,窥视着其他行色匆匆的乘客。确定没人跟踪后,才重新往前走。
他朝选择碰面的廉价咖啡馆走了过去。和以往每次接头一样,他没有立刻走进去,而是站在街对面的公交车站盯着咖啡馆的入口。他确信自己已经甩掉了尾巴,但还得看看沃纳有没有被人跟踪。
他不知道他是否认得出已经二十岁的弗兰克·沃纳,他俩上次见面还是六年前。沃纳也同样无法确定能不能把他认出来。于是两人约定把当天的《柏林摩根邮报》打开到体育版。沃洛佳看着一篇足球新赛季的前瞻报道,不时抬起头看沃纳来了没来。在柏林读书时,沃洛佳是柏林成绩最好的柏林赫塔队的球迷。他经常放声高唱:“前进!前进!柏林赫塔!”他很想知道这支球队的前景,但等人的焦急打断了他的专注力,他一遍遍地看着这篇报道,里面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在西班牙的两年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促进他的事业——情形恰恰相反。沃洛佳发现了不少类似海因茨·鲍尔这类纳粹安插的“志愿兵”,但苏联秘密警察随后以纳粹奸细为名,逮捕了大量仅仅对共产主义抱有微词的真正“志愿兵”。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几百名抱着理想而来的有志青年被折磨致死。相比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似乎对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更加感兴趣。
志愿军的努力徒劳无功。斯大林的政策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内战以叛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苏联最不想见到的右翼法西斯支持者建立了西班牙独裁政权。那些被派到西班牙参战的人,尽管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却承担了所有失败的后果。其中一些人回到莫斯科就失踪了。
马德里陷落以后,沃洛佳带着恐惧不安的心情回到莫斯科。他发现这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斯大林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对红军进行了清洗,几千个指挥官不知所踪,其中包括不少和父母同住在政府公寓的红军高层。格雷戈里·别斯科夫这类原本靠边站的人却得到了重用,他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沃洛佳的父亲现在主管莫斯科的防空工作,一天到晚都非常忙。他的得势也许是沃洛佳没有成为斯大林在西班牙失败政策替罪羊的最主要原因。
伊利亚·德沃尔金不知怎地也逃过了处罚。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娶了沃洛佳的妹妹安雅。这让沃洛佳耿耿于怀。谁也无法解释安雅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安雅已经怀孕了。沃洛佳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安雅给一个贼眉鼠眼的婴儿喂奶的可怕情形。
休息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沃洛佳就被调往柏林验证他的价值去了。
他把目光从报道上移开,看见沃纳沿着街道朝咖啡馆走来。
沃纳的变化不大。他长高长壮了,但额前垂下的那撮栗色卷发,蓝色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幽默还是让少女们为之痴狂。他穿着淡蓝色的薄外套,袖扣上的金链闪闪发光。
没有人跟踪沃纳。
沃洛佳穿过马路,在沃纳抵达咖啡馆之前拦住了他。沃纳张口大笑,露出一口大白牙。“你头发剃那么短,我都认不出你了,”他说,“很高兴在这么多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你。”
沃洛佳发现,沃纳还是以前那个沃纳,热情和魅力依旧。“我们进去吧。”
“你不是真的想进那个垃圾场吧,”沃纳说,“里面都是些吃蘑菇猪肉肠的乡巴佬。”
“我不想在街上久留,会被任何一个路过的人发现。”
“再过三个门洞有一条小巷。”
“我们就去那吧。”
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走进堆煤场和杂货店中间的一条小巷。“最近你在忙什么?”沃纳问。
“和你一样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沃洛佳权衡着是不是要告诉他更多有关自己的事情,“我去了西班牙。”这点没什么好隐瞒的。
“和我们在德国的斗争一样,你们在西班牙也失败了。”
“但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远没完呢!”
“问你一个问题,”沃纳靠在墙上说,“如果你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邪恶的话,你愿意做反苏的间谍吗?”
沃洛佳想说:不,绝对不想!话还没说出口,他突然意识到这么说太生硬了——为了理想背叛祖国不正是他让沃纳做的吗?他怎能想当然地说自己不愿意呢?“我说不清,”他说,“即便痛恨纳粹,让你做针对德国的工作一定也很难。”
“你说得对,”沃纳说,“战争爆发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会帮你杀死德国的士兵,轰炸德国的城市吗?”
沃洛佳很担心。沃纳似乎比以前软弱了不少。“这是战胜纳粹的唯一途径,”他说,“你很清楚这一点。”
“是的。很久之前我就下定了决心。这些年来,纳粹变本加厉,我的决心也一直没有变。但老实说,和他们对抗非常难。”
“我明白。”沃洛佳同情地说。
沃纳说:“你让我再找些别的人做你让我做的事,是吗?”
沃洛佳点了点头:“是的,比如说威廉·伏龙芝。你记得他吗?学校里最聪明的那个男孩。伏龙芝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被冲锋队员破坏的会议正是他主持的。”
沃纳摇摇头说:“你指望不上他了,他去了英国。”
沃洛佳心一沉:“为什么要去英国?”
“他是个物理学者,现在正在英国进修。”
“真该死!”
“我帮你想到了另一个人。”
“很好。”
“你认识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吗?”
“不怎么认识,他是我们学校的吗?”
“不是,他读的是天主教学校。那时他和我们的政治观点也不一样。他的父亲是中央党的大人物。”
“就是1933年协助希特勒掌权的中央党吗?”
“是的。那时海因里希为他父亲工作。他父亲现在加入了纳粹党,但海因里希却充满了罪恶感。”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醉酒后把心里的郁闷告诉了我妹妹弗里达。我妹妹今年十七岁,我想他喜欢她。”
沃洛佳精神一振,这的确是个突破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你为何觉得他会为我们工作?”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有机会通过做间谍的方式和纳粹斗争,你愿意为苏联做间谍吗?’他说愿意。”
“他是做什么的?”
“他在军中服役,但他的肺有毛病,因此担任文书的工作——这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现在他在德军经济计划和采购部门工作。”
沃洛佳备受感动。这样的人一定确切地知道每个月德军卡车、坦克、机关枪、潜水艇的增加数量——知道德军把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他感到非常兴奋。“什么时候能让我见见他?”
“马上就可以。我约了他下班后在阿德隆饭店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