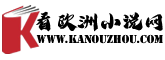第7章 1933年,柏林(7)
“他肯定会去。”伊娃说,“只要有人生病,他就会竭尽全力治疗。”接着她语带轻蔑地说,“无论种族和党派,他都以病人为先,我们可不是纳粹!”说完她走出了接待室。
埃里克觉得很委屈,他没想到这身制服会给他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学校里所有人都觉得这制服很好看。
过了一会儿,洛特曼医生出现在诊疗室门口。他对两个候诊的病人说:“很抱歉,有人临盆了,我会尽快回来。”接着,他看了一眼埃里克,说:“来吧,小伙子,坐我的车吧,即便你穿着这身制服。”
埃里克跟着他走出诊所,坐进了“三条腿青蛙”的副驾驶座。埃里克很喜欢汽车,希望尽快能到开车的年龄。平时,坐各种车都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会好奇地看着汽车上的各种按钮,认真学习开车的技巧。但穿着青年团的制服坐在犹太医生旁边,却让他像件展品一样难受。如果被李普曼先生看到该怎么办啊?一路上,他都很苦闷。
好在不远,没几分钟,汽车就开到了冯·乌尔里希家门口。
“生孩子的女士叫什么名字?”洛特曼问。
“艾达·汉普尔。”
“没错,上星期她来过。婴儿早产了,快带我去见她。”
埃里克带医生进了屋。他听到一阵啼哭声,孩子已经生了!他连忙冲到地下室,医生跟着他。
艾达仰面躺在床上。床单已经被血和其他东西浸湿了。卡拉怀抱着婴儿站在床边。小婴儿身上裹着一层黏液。艾达的裙子底下有一根粗绳似的东西,连在婴儿身上。卡拉害怕地瞪大了双眼。“我做得对吗?”她大声问。
“你做得很对,”洛特曼医生的话让她安下心来,“再抱一会儿婴儿。”他坐在艾达身边,听了听她的心跳,摸着她的脉搏,问:“亲爱的,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很累。”艾达说。
洛特曼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站起身,看了看卡拉怀中的婴儿。“孩子很小。”他说。
埃里克五味杂陈地看着医生打开包,拿出几根线拧成了一条绳子,然后在绳子上打了两个绳结。医生给绳子打结的时候轻声对卡拉说:“为什么哭啊?你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你凭一己之力接生了一个孩子!我不来你也能做得很好。长大以后,你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卡拉平静了些。她小声说:“医生,你看看他的头,”医生凑到她跟前才听清她说了什么,“这孩子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让我看看。”医生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在绳结间把绳子剪成两截,然后从卡拉手里接过光溜溜的孩子,把他举在跟前仔细端详。埃里克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但是婴儿那么红、那么皱、那么瘦,实在不好说。然后,医生想了一会儿,说:“哦,亲爱的。”
再仔细一瞧,埃里克发现了一点不对劲。婴儿的脸两边不匀称。其中一侧正常,另一侧却凹下去一块,眼睛看上去也有点奇怪。
洛特曼让卡拉继续抱着小婴儿。
艾达又开始呻吟了,她看上去的确很累。
等她放松下来,洛特曼伸手到她的裙子底下,拿出一团东西,有点像肉,让人恶心。“埃里克,”他说,“拿张报纸来。”
埃里克问:“哪种报纸?”他的父母每天都会把所有主流报纸带回家。
“小伙子,任何一种都行,”洛特曼温和地说,“我只是拿来包东西。”
埃里克跑上楼,找了张前天的《福斯日报》。他回到地下室,洛特曼用报纸包住了那团肉一样的东西,放在地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胎盘,”他对卡拉说,“待会儿最好烧掉它。”
接着,他又坐到床边。“艾达,我亲爱的姑娘,你表现得非常勇敢,”他说,“你的孩子活下来了,但他似乎生病了。我们把他洗一洗,包得暖和点,然后带他去医院。”
艾达很害怕。“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必须带他到医院检查。”
“他会好起来吗?”
“医院里的医生会尽力诊治,其他的我们就交给上帝吧。”
埃里克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洛特曼说:“艾达,你觉得自己能起床和我一起去医院吗?孩子需要妈妈喂。”
“我太累了。”艾达又说了一遍。
“再歇一两分钟,但不能太久,婴儿需要马上就诊。卡拉会帮你穿好衣服。我先上楼了。”然后,他转向埃里克,玩笑似的说:“纳粹小子,跟我上楼去吧。”
埃里克真想挖条地缝钻进去。洛特曼医生的宽容比洛特曼夫人的斥责更让他难受。
他们正要离开时,艾达叫住了医生。
“亲爱的,有事?”
“孩子叫库尔特。”
“这名字很棒。”说完,洛特曼医生便带着埃里克离开了。
劳埃德为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做助理的第一天,正赶上新一届议会成立首日。
沃尔特和茉黛拼命工作,希望挽救德国脆弱的民主。劳埃德很理解他们的绝望,一方面因为沃尔特夫妇是他从小就认识的好人,另一方面是他很怕英国会步德国后尘,走上一条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选举没解决任何问题。纳粹获得了百分之四十四的相对多数票,但仍少于他们希望达到的百分之五十一。
沃尔特看到了希望。他在开车前往议会开幕式的路上,对埃里克说:“即便用上高压手段,他们也没能赢得多数德国人的选票。”说着,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方向盘,“不管他们说了什么,纳粹都不受欢迎。他们在政府的时间越长,人民就越能看清他们的嘴脸。”
劳埃德没有这么确定。“纳粹关闭了反对党的报社,把议员关进监狱,贿赂警察,”他说,“怎么还会有百分之四十四的选民投他们的票呢?我不觉得这个结果能让人安心。”
议会大厦烧毁严重,完全不能用了。于是开会地点选在了科尼格广场对面的国家歌剧院。这是一座综合性大剧院,有三个音乐厅、十四间小剧场,外带餐厅和酒吧。
他们刚到,就被剧院周围的情况吓了一跳。冲锋队员把整座大剧院包围了。议员和他们的助理站在入口处,试图进去。沃尔特生气地说:“希特勒现在是想通过阻挠我们进场,来为他自己开路吗?”
劳埃德发现,所有的门都被冲锋队员堵住了。他们把穿着纳粹制服的人放进去,其他人却得出示证件。一个年纪比劳埃德还小的少年轻慢地打量着劳埃德,然后不太情愿地把他放了进去。这是种赤裸裸的恐吓。
劳埃德觉得自己快要炸了,他最讨厌被恐吓。只要来个左勾拳,他就能把这个冲锋队少年打翻在地。不过他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转身走了进去。
那次,在人民剧院打完架以后,艾瑟尔检查了劳埃德头上鸡蛋大小的肿块,让他赶快回英国去。他说服了母亲,可以晚点动身,但回英国是迟早的事。
艾瑟尔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其实他知道。有时他的确很害怕,但这只会激起他的斗志。直觉让他发起进攻,而不是选择后退。这点让艾瑟尔非常担心。
讽刺的是,事到临头,艾瑟尔也一样。虽然害怕,但留在柏林见证德国的历史性转折让她激动不已,她也因为纳粹实施的暴力和压迫而义愤填膺。艾瑟尔决心写一本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专著,用以警示其他国家的民主人士。“你比我更容易招来危险。”劳埃德曾对她这样说过,可她就是不听。
歌剧院里面站满了冲锋队员和党卫军的人,许多人都带着武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表情和举止都是对反纳粹者的憎恨和不屑。
社会民主党的小组会,沃尔特迟到了。劳埃德焦急地在里面到处找开会的房间。他往辩论厅里看了一眼,发现一面巨大的纳粹十字旗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占满了整个大厅。
下午大会开始后的第一个议程将是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可以使希特勒内阁在没有议会的授权下通过新的法律。
授权法案为德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希特勒将彻底地成为一个独裁者。过去几周的镇压、凌辱、暴力和苦难将永远存在下去。简直无法想象。
劳埃德想象不出哪一国的议会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这相当于让议员投票表决剥夺自己的参政权。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杀。
他在一个小剧场里找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社会民主党的内部会议已经开始。劳埃德匆忙把沃尔特引入会场,然后就被派去倒咖啡了。
在冲咖啡的队伍中,劳埃德发现在自己前面的是一个脸色苍白、表情机警、一身黑的年轻人。劳埃德的德语比以前流利很多,他有足够自信和陌生人攀谈了。通过交谈,劳埃德得知,黑衣年轻人叫海因里希·冯·凯塞尔,和他一样是没工资的助理,而海因里希为他的父亲工作,天主教中央党议员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
“我爸爸和沃尔特·冯·乌尔里希很熟,”海因里希说,“1914年,他们都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做过随员。”
政治和外交界的圈子可真小,劳埃德心想。
海因里希告诉劳埃德,回归基督教的信仰是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良方。
“我不怎么喜欢教徒,”劳埃德诚实地说,“请别介意。我外公是威尔士的福音传道者,我妈妈却对宗教不以为意。我继父是个犹太人。我们周末时常会去阿尔德盖特的圣公会教堂做礼拜,因为那里的牧师是个工党党员。”
海因里希笑了笑说:“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祈祷的。”
劳埃德记得,天主教徒不会说服别人改变信仰。阿伯罗温老家的外祖父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觉得世间唯一的真理就是那几卷福音书,任何不信福音的人都将受到诅咒。
回到内部会议会场时,沃尔特正在发言。“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他说,“通过这样的宪法法案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在场,这就要求647名代表中有432名在场。另外,在场的代表中也必须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
放下托盘的时候,劳埃德在脑海中简单计算了一下议员的人数比。纳粹党有288个议席,和他们结盟的民粹党有52个议席,总共是340张赞成票——这比法定多数还差将近一百票。沃尔特说得对,授权法案不可能通过。劳埃德宽心了一点。他坐下听讨论,顺便提升一下自己的德语水平。
但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别这么确定,”一个操着柏林工人阶级口音的代表说,“纳粹和中央党高层达成了交易。”劳埃德想起,中央党就是海因里希为之服务的政党,“这样他们又能多得74票。”这个男人说。
劳埃德皱起了眉。中央党为什么会支持一项剥夺他们权益的法律呢?
沃尔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样的想法。“天主教徒怎么会这样蠢呢?”
劳埃德希望在倒咖啡前就知道这件事,那样就可以跟海因里希辩个明白了。也许还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呢!真该死!
操着柏林口音的男人说:“意大利的天主教政党和墨索里尼达成了协议——一项保护教堂的协定。这里的情况也一样。”
劳埃德算了算,中央党的支持将使纳粹的票数达到414票。“仍然没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他如释重负地对沃尔特说。
一个年轻的助理听到他的话,向大伙澄清道:“你们难道把议长最近的宣言忘了吗?”德国议会的现任议长是希特勒的亲密同伴赫尔曼·戈林。劳埃德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份宣言。其他人似乎也没听过。议员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位助理继续向大家解释:“他剥夺了缺席的共产党议员的投票权,因为他们都被投入了监狱。”
全场响起愤怒的抗议声。劳埃德发现沃尔特的脸涨得通红。“他无权这么干!”沃尔特说。
“这完全是非法的,”助理说,“但他就是这样做了。”
劳埃德非常失望。法律能够如此儿戏吗?他又做了番计算。共产党拥有81个议席。如果他们的票数不算,纳粹只要达到566票的三分之二,也就是378票就行了。纳粹党和民粹党的总票数加起来不到378票——但如果有中央党的支持,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将取得议会的多数。
有人说:“这完全是非法的,我们应该以缺席抗议!”
“不能这样做!”沃尔特慷慨激昂地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法案了。我们应该说服中央党的天主教徒们。韦尔斯必须马上去见卡斯。”奥托·韦尔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首,路德维希·卡斯是中央党的党首。
会场里响起一阵附和声。
劳埃德做了个深呼吸,镇静地对沃尔特说:“乌尔里希先生,你何不跟戈特弗里德·冯·凯塞尔吃顿午饭呢?我没记错的话,战前你们曾在伦敦一起工作过。”
沃尔特哑然失笑道:“那个讨厌的家伙!”
也许共进午餐不是个好主意。劳埃德说:“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他。”
沃尔特想了想说:“我讨厌他——但我向上帝起誓,我愿意做一切尝试。”
劳埃德问:“要我向他发出邀请吗?”
“好吧,那就试一试。如果他肯接受,告诉他一点钟在赫仑俱乐部见面。”
“知道了。”
劳埃德赶到海因里希刚才进入的小会场,急步走了进去。一场类似于社会民主党小组会的讨论正在进行。劳埃德环顾会场,看见了一袭黑衣的海因里希,和他对视一眼,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出来。
走出会场后,劳埃德对海因里希说:“据说你们这边会支持授权法案。”
“尚不确定,”海因里希说,“意见还没有统一。”
“哪些人反对和纳粹合作?”
“布鲁宁和其他人。”布鲁宁是前总理,在中央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劳埃德感觉到了希望。“还有些什么人?”
“你把我叫出来是为了套我的话吗?”
“对不起,当然不是。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想和你父亲共进午餐。”
海因里希一脸狐疑。“他们不是朋友——你应该很清楚,不是吗?”
“我听说了,但今天他们应该把私人恩怨抛在一旁!”
海因里希不是很确定的样子。“我去问问他吧,稍等。”他转身走进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