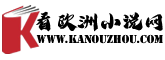第3章 1933年,柏林(3)
冲锋队的口号变了:“捣毁犹太人的报纸!”队员们异口同声地呼喊着。有人开始扔东西,一棵烂菜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门口溅了一地。让卡拉害怕的是,他们很快把矛头转向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她连忙后退,透过窗角偷偷朝外张望,希望冲锋队员们没看见她。他们在大楼外面停住脚步,嘴里仍然喊着口号。有个人朝楼上扔了块石头,砸中了母亲办公室的窗玻璃,幸好玻璃没碎,但卡拉还是害怕地轻轻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有个戴着红色软帽的打字员进来了。“怎么啦?”她问卡拉,然后朝外看了一眼,“哦,天哪!”
冲锋队员们走进大楼,楼梯上响起他们的脚步声。卡拉害怕极了:他们会干些什么啊!
施瓦布中士走进母亲的办公室。他犹豫了一会儿,看见办公室里只有卡拉和打字员以后,放松了下来,拿起打字机就往窗外扔,打字机破窗而出,摔到楼下,玻璃碎了一地。卡拉和打字员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更多的冲锋队员喊着口号进来了。
施瓦布抓住打字员的胳膊问:“亲爱的,办公室的保险箱在哪儿?”
打字员惊恐地回答说:“在档案室里。”
“带我过去。”
“好,都听你的。”
施瓦布拽着她出去了。
卡拉哭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停了下来。
她想躲在桌子下面,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想在这些人面前露怯。内心的某种东西让她想进行反击。
但她该怎么办呢?她决定去提醒母亲。
她走到门口,看了看走廊。冲锋队员们在几个办公室之间进进出出,但还没有走到尽头的那几间。卡拉不知道会议室里的人有没有听到动静。她拼尽全力沿着走廊跑,但一阵尖叫让她站住了。她向声音传来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发现施瓦布正用力摇晃着戴软帽的打字员:“快告诉我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发誓说的是实话。”打字员哭着说。
卡拉气极了,施瓦布没权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她大声喊:“施瓦布,你这个小偷,不准碰她。”
施瓦布恨意满满地看着她,卡拉心一凉,满心都是恐惧。接着施瓦布把目光投向卡拉身后的一个人:“把这孩子给我拎出去。”
卡拉被人从后面提了起来。“你是小犹太人吗?”这男人问,“你满头都是黑发,一看就是个小犹太崽子。”
卡拉吓坏了。“我不是什么犹太人。”她尖叫着。
冲锋队员把她抱过走廊,送进了母亲的办公室。卡拉蹒跚几步,跌倒在地。“给我老实待着。”说完他就走了。
卡拉站起身,她没有受伤。走廊里都是冲锋队员,卡拉没法找到母亲,但必须找人帮忙。
卡拉朝打碎了的窗户外面看去。街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两个警察正站在旁观的人群中闲聊。卡拉朝那两个警察大喊:“警察先生,快救命啊!”
他们看着卡拉,笑了。
笑声激怒了她,怒气使她胆大了许多。她往办公室门外张望,偶然间看见了墙上的火灾警报器。她走到警报器前,抓住把手。
卡拉犹豫了,没有火灾绝不能拉响警报器。墙上贴着的告示上说,乱拉警报将受到可怕的处罚!
但她还是拉下了把手。
一开始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警报器可能坏了吧,卡拉心想。
很快,此起彼伏的电喇叭声便响彻了整栋大楼。
记者们立刻从走廊那头的会议室跑出来,约克曼是第一个。“发生什么事了?”他扯着嗓门怒气冲冲地问。
一个冲锋队员说:“你们这些犹太共党分子办的破杂志侮辱我们的领袖,我们要关闭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冲锋队员不顾他的阻挠,闯进了侧面的一间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和像是金属台面被推翻的声音。
约克曼转身对一位下属说:“施奈德,赶快把警察叫来。”
卡拉知道叫警察没用,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却什么都没有做。
母亲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沿着走廊往前冲。“你没事吧?”她一把搂住了卡拉。
卡拉不希望母亲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个孩子。她推开母亲,说:“别担心,我很好。”
母亲四处看了看:“我的打字机呢?”
“他们把你的打字机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卡拉马上想到,妈妈再也不会因为打字机按键的操纵棒搅合在一起而迁怒于她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母亲抓起桌子上的相框,拉着卡拉的手,匆忙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冲下楼梯时,她们并没受到冲锋队员的阻拦。在她们的前方,一个可能是记者的健壮男子抓住一个冲锋队员的衣领,拉着他出了大楼。母女俩跟着这两人走出来。另一个冲锋队员紧跟在她们身后。
男记者把冲锋队员拖到两个警察面前。“请以抢劫的名义逮捕他,”记者说,“他抢的一罐咖啡还在衣袋里呢!”
“放开他。”较年长的警察说。
记者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冲锋队员的衣领。
跟在卡拉和母亲身后的冲锋队员站到了同伙身边。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刚松开手的记者。
“我叫鲁道夫·施密特,是《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派驻在议会的首席记者。”
“鲁道夫·施密特,我以袭警的罪名逮捕你。”
“太荒唐了,我抓住了正在偷窃的小偷。”
年长的警察对两个冲锋队员说:“把他带到派出所去。”
两个冲锋队员架住了施密特的胳膊。施密特起先想反抗,但马上改变了主意。“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将出现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他说。
“不会有下一期杂志了,”警察说,“把他带走。”
消防车到了,十几个消防队员从车上跳了下来。消防队长飞快地对警察说:“我们要对这幢大楼进行清场。”
“回你们的消防队去,这里没什么火情,”年长的警察说,“只是冲锋队在关闭一家共产党的杂志社而已。”
“这和我无关,”消防队长说,“警报器响了,我们就得把所有人都撤出来,就算是冲锋队员也得从楼里出来。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们能对付!”说完他带着部下进了大楼。
卡拉听见母亲在喊:“哦,不。”她转过身,看见母亲正瞪着人行道上散了架的打字机。打字机的金属面板脱落下来,露出连接按键和金属杆的连接带。键盘已经被摔得不成形了,滚筒的一端脱落了,换行时会响的小铃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打字机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但母亲看起来像是要哭了。
冲锋队员和杂志社员工在消防队员的簇拥下走出大楼。施瓦布中士强辩道:“根本没有什么火灾!”消防队员却只是一个劲地把他往外推。
约克曼走到母亲面前说:“他们没来得及造成很大的伤害——消防队阻止了他们。按下报警器的人立了大功!”
卡拉原本担心会因为假报火警而受到责怪。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
她拉起母亲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似乎能暂时使母亲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反常的行为说明她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要是卡拉哭,母亲一定会让她用手绢擦的。“我们该怎么办啊?”母亲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她总是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卡拉注意到近处站着两个人。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和妈妈年龄相仿、很有气势的漂亮女人。卡拉见过她,但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了。站在旁边的男孩,从年纪上看,像是她的儿子。男孩不是很高,瘦瘦的,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他的面容很清秀,只是鼻子塌了,有点破相。面对此情此景,两位来客都很惊奇,男孩更是被气坏了。
女人开了腔,她用的是英语。“茉黛,你好,”卡拉觉得她的声音有些许耳熟,“你没认出我来吗?”她说,“我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这是我的儿子劳埃德。”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柏林找了家不用花多少钱就能练一小时拳击的俱乐部。俱乐部位于工人阶级聚集的城北维丁区。他练了会儿实心球,跳了会儿绳,打了会儿沙袋,然后戴上头盔,在绳圈里打了五个回合。俱乐部教练为他找了个年龄和体形都差不多的对手——劳埃德是个次重量级拳手。德国拳手经常能出其不意地出拳,没几个回合,劳埃德就挨了好几下。躲闪一番以后,劳埃德突然打了记左勾拳,把对手打翻在地。
劳埃德生长在伦敦东部一个民风凶悍的街区里。十二岁时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继父伯尼·莱克维兹对他说,“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肯定会被班里的刺头挑出来欺负。”被劳埃德唤作“爸爸”的伯尼是犹太人——他的母亲只会说意第绪语。伯尼把劳埃德带到了阿尔德盖特拳击俱乐部。艾瑟尔反对这么做,但伯尼没有听她的,这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多见。
劳埃德学会了迅速移动、狠狠出拳,很快就没人敢欺负他了。他的鼻子经常被打碎,以至于不再像以前那么英俊了。然而劳埃德发现自己具有拳击方面的天赋。他反应很快,冲劲十足,经常在绳圈里把对手打倒。劳埃德没有选择转入职业拳坛,而是打算进剑桥大学深造,这让俱乐部教练非常失望。
劳埃德冲了个澡,穿上衣服,走进一间工人们经常聚会的酒吧,买了杯生啤酒,坐在吧台前,给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写信,把自己和冲锋队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告诉她。米莉对母亲带劳埃德去柏林很妒忌,劳埃德答应写信告诉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劳埃德被这天早上的冲突吓得不轻。政治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母亲艾瑟尔是英国议会的议员,父亲伯尼是伦敦市的市议员,他本人是伦敦劳动青年联盟的主席。但至今为止,他眼中的政治只是辩论和选举。他从没见过穿着制服的恶棍在警察的微笑纵容下胡作非为。这种撕下和善伪装的政治,把他吓坏了。
“米莉,伦敦会发生这种事吗?”他在信中问。直觉告诉他这种事完全不可能。但希特勒在英国的实业家和报业寡头中很有人气。几个月前,一身匪气的下院议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4]创立了英国法西斯同盟。和德国的纳粹党人一样,他们喜欢穿着军装上蹿下跳。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写完信,劳埃德把信折起来,乘地铁回到了市中心。他和母亲将和沃尔特·乌尔里希夫妇共进晚餐。劳埃德经常听母亲说起茉黛的事情。母亲和茉黛是地位悬殊的朋友:艾瑟尔在茉黛家的大宅子里当过女佣。之后她们却一起参政,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斗争期间她们创立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女性报纸。后来她们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渐渐疏远了。
劳埃德清楚地记得1925年去乌尔里希家的伦敦之行。那时,五岁的埃里克和三岁的卡拉都学会了德语和英语,而他却只会一门英语,这让他颇为尴尬。也正是在那次伦敦之行中,艾瑟尔和茉黛和解了。
劳埃德走进罗伯特酒馆,里面摆放着长方形的桌椅和装饰着彩色玻璃的铁制灯座,内部装潢非常精致。可最让他倾心的还是盘子旁边直立着的浆白色餐巾纸。
母亲和乌尔里希夫妇已经先到了。走到桌前,劳埃德才意识到两位女士打扮得非常动人:两人都姿态优雅,衣着华贵,美丽而自信。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们。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对时尚的把握有多少是从这位贵族朋友那儿学来的。
点完了菜,艾瑟尔解释了她的来意。“1931年我落选了议员,”她说,“我想在下次竞选中赢回来,但我还要养家。幸运的是,茉黛,你教会我怎么做一名记者。”
“我没教你什么,”茉黛说,“你本身就有当记者的才能。”
“我正在为《新闻纪事报》撰写有关纳粹的系列报道,我还和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签了合同,要为他写本书。我让劳埃德来这儿当我的翻译——他正在学法语和德语。”
劳埃德发现母亲笑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夸赞。“我的翻译技能没经过多少实践检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见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劳埃德点了在英国没吃过的裹着面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觉得这道菜非常美味。吃饭时,沃尔特问他:“你可以不去上学吗?”
“妈妈觉得这样学德语能更快些,学校也同意让我来。”
“到议会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能整天都说德语,只是我不能付给你工资。”
劳埃德激动起来:“太好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还需要艾瑟尔同意。”沃尔特补充道。
艾瑟尔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你可得给他放假哦!”
“这是自然。”
艾瑟尔把手伸过桌面,碰了碰沃尔特的手。这是种相当亲密的姿态,劳埃德意识到三个大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沃尔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尔说。
“对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我是来者不拒的。”
艾瑟尔说:“我对政治有点看不懂了,德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啊?”
茉黛说:“20年代中期这里一切都还好,德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把一切全毁了。现在我们正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她的声音似乎因为悲愤而颤抖着,“上百人排队竞争一个工作机会。我观察着他们的脸,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里的孩子。这时纳粹给了人们希望,而那些人会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沃尔特似乎觉得她夸大了事实。他故作轻松地说:“好在希特勒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上次选举时,纳粹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他们的票数最多,但领导的是个少数派当权的政府。”
“这就是希特勒要再进行一次选举的原因,”茉黛插话说,“他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把德国变成他想要的野蛮的极权国家。”
“他能达到目的吗?”艾瑟尔问。
“当然不能。”沃尔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尔特说:“我不相信德国人会为独裁投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