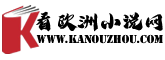第408章 应采薇的回忆(一)
我叫Vivian,中文名字叫做应采薇。我生在美国,是这个国家的第二代移民。
我曾经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父亲是大学里研究纳米技术的教授,年轻有为。在他很多同龄人还在各大实验室中祈祷明天能出一个理想一些的实验结果,以及筹谋下一个博士后该去哪里做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终身教职。
母亲自小学习美术,画得一手好画,是个善良又精致的天使。平日里除了在家照看我和作画之外,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少儿救济院,去那里做义工。而等我长大了一些之后,也经常跟在她后面跑去救济院里帮忙,嗯,当然更准确地说是去玩。
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对既可爱又美丽的双胞胎孪生姐妹——卡门和路易斯。
我本以为我的生活会一直这么继续下去:有疼爱我的父母、有友爱的小伙伴。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幸福并不是什么必然而恒久的东西,它只是一件迷人却又无比脆弱的奢侈品,外界随便的那么一击就会将它撞得粉碎……
噩耗传来的那一天,我和母亲同往常一样,正在救济院里各忙各的事。
突然有电话打来,是来自警局的通知。在外地开会的父亲遭遇抢劫,案发时间初步估计是在午夜。也正因为此,发现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迹象……
我的生活自此开始变得灰暗,一切都脱离了它原来的轨道。
母亲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击倒,大病了一场。
等到她好不容易慢慢康复,却被诊断出患上了抑郁症。她终日心情低落,以前总是挂在脸庞上的美丽笑容再也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微微泛着泪光的忧伤的眼神。
几年后的一天,母亲终于吞下了整瓶的安眠药,带着安详而温柔的微笑永远离开了我。
对此我曾经有过怨恨,为什么母亲会选择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直到后来我整理母亲遗物时,在她的画室中发现了一本手写的日记,我才从那些笔迹凌乱的字里行间读懂了母亲在这些年里究竟是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原来对于父亲的死,人们在背后还悄悄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
父亲并不是意外地死于抢劫——这个警方给出的结论。因为那样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只想要捞点现金的劫匪会对父亲带去开会的研究资料感兴趣。而那只丢失的笔记本和凶手一样,就象是从人间蒸发了似的,再也找不到半点的踪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是谁最先用如此恶毒的用心来揣测这整件事情,总之,等谣言流传到母亲这里时,已经变得有模有样:父亲其实是假借开会的名义,想把他们实验室里最新的研究成果偷偷贩卖给某一方未知的势力。只是在那中间却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纠纷,最后就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被杀人越货了账。
我当然相信父亲不是那样的人,母亲自然是比我更加了解父亲的为人。可是对于这来自背后的指指点点,母亲无从辩白。
日复一日,她所能承受的压力终于到达了临界点,于是她只好选择了离开这个令她失望的世界。
我总觉得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是见到了父亲前来接她,她问到了真相,也得到了最后的安慰,所以,她才会带着笑容离开。
或许对于母亲来说,这样的结局并非不好,这种解脱更符合她艺术的气质。
只是,在我,我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要象我的名字一样,要充满活力的、过好我的每一天!
和许多中国父母一样,在我还没出生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就已经开始为我准备读大学的教育基金。
如果没有这些变故,我想我很可能会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努力考进哈佛医学院。然后考取行医执照,在某一家医院里当二十四小时待命的住院医生。最后,存下钱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诊所。
只是生活没有如果。
所以,后来我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毕业之后能够成为一名记者。
我要用我的笔来记录那些真实,要让那些有话想说的人找到一个可以大声说话的地方。当然,我也有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是异想天开的想法,那就是或许有一天,我能亲自解开当年父亲发生意外的真相。
我就读的大学在洛杉矶。大城市的治安当然要差一些,但那是父亲遇害的城市,因此,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父母留下的教育基金当然远不够支付全部的学费。因此,在申请了奖学金和学生贷款之后,我还必须要在外面做兼职才能补足我剩下的生活费。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卡门和路易斯选择了和我一起来到这座陌生而危险的城市。
虽然她们嘴上说的是,大城市的机会更多,又有谁不想多开开眼界呢。但是我很明白,她们是不放心我一个人,而且三个人一起住,能省下不少的房租来呢。
接下来的几年,虽然辛苦忙碌,但同时也很充实。
找兼职,最是麻烦。在打了几次短工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给房屋中介公司管理出租的房子。然后一干就是两年多。
功课,最是辛苦。可好在付出必然有回报,必修课一门一门地拿下,成绩都还不错。在一次实习中,因为表现不俗给一家报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方希望我可以在毕业之后去他们那里工作。我当然是欣喜不已。
爱情,来得突然又让人不能抗拒。一次偶然的合作,我结识了鲁文。之后他很迅速地就成了我的男朋友。
相对来说,倒是友情十数年未变。卡门和路易斯,这两个救济院长大的孤儿已然成为我的家人。
在卡门姐妹默默支持了我那么久之后,我很希望能在我正式上班之后,为她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而她们姐妹在也打算在附近的社区大学读点什么,只是一时间她们还没想好以后要干什么而已。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不是吗?
然而,天意总是弄人。
就在我相信明天会更好,满怀希望等待更好的生活来临的时候,我的好运气似乎用到了尽头。
二零一四年的元旦刚过完,新年去上班的第一天就莫名其妙地被房屋中介公司的老板炒了鱿鱼。据老板说,那是因为客户投诉我的工作。只是我并不相信而已。
同那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同事相比,公司的客户明显更喜欢我一些。没有理由他们都没事,而我却被人投诉了呀。虽然之前我的工作是出了一些奇怪的差错,但是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寻找问题的根源了。
不过显然老板不愿意给我这个补救的机会罢了。
突然间失去了一份已经做得熟门熟路的工作,我当然也觉得懊恼。不过总的来说,我并不会觉得非常的沮丧。毕竟家变之后,我已经被生活催着要提前长大。
说到底这也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东家打不成了,还有西家可以打嘛。再说,就算不被炒掉,最多也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等拿了毕业证书,我也得自己交辞职报告才好去报社上全职的班。
唯一麻烦的是,感恩圣诞季刚过完,市面上的临时工作可实在不多。幸好,卡门姐妹在餐馆做伺应生,对相关的行当消息比较灵通。不过一两天的时间,帮我找了个在酒吧的兼职。
虽然那个酒吧的位置不是特别好,离公寓有些远,而且附近也没有比较方便的公共交通,但是能那么快就找到工作,我已经觉得万分的走运。至于其它的小小问题,又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呢?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庆幸上多久,悲剧就发生了。
到酒吧上班之后,没几天,我临时帮人顶了个晚班。打烊后已过午夜,加上天冷,还不是周末,街上的路人就越发的稀少。
因为这一路上相对还算安全,既没有小混混们喜欢聚集的路口,也没有处于叛逆期孩子愿意流连的小广场,所以我打算按着才养成的习惯步行走回公寓,而没有要鲁文特地开车来接我。
几分钟后,一场突发的车祸告诉我,我这个自以为是不矫情的决定错得有多么的严重。
是的,就在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寒冷的冬夜,我在一个僻静而又昏暗的拐角处,被一辆有超速嫌疑的车子迎面撞了个正着。
本来好端端地走着路,被车撞上,已经是倒霉到家的事了,可是祸不单行的是,还碰上了个无良的肇事司机。意外发生后,那个司机既没有报警,也没有叫救护车,而是选择了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任由被当场撞昏的我躺在冰冷的街头上。
更要命的是,因为天寒地冻,附近的居民大多早已经紧闭门户呼呼入睡了,根本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交通意外。
如果不是卡门姐妹觉得我过了应该回家的点,却还迟迟没有到家,打电话又没人接听,她们两个放心不下,才一路找过来的话,我猜我已经一命呜呼了。而直接的死因并非是大力撞击,而应该是被冻死的才对。
即便如此,等我被送到医院时,据说整个人都还是给冻僵直了。
急诊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天快亮了,医生才最后宣布,把我的小命给捡了回来。
命虽然是保住了,可是清醒过来的我,却发现在腰椎以下竟然再也没有一点的知觉!
据医生说,那是因为我被撞飞出去后,腰部首先撞上了街边的巴士站牌,这样脊椎中的神经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至于这种没有感觉,是暂时的功能性障碍,还是永久性的器质性损伤,一时半会的就没有人能下定论了。
我在医院病房里呆了大约一个星期不到的样子,因为生命体征都很稳定,便被要求出医院,回家静养了。
休息了几个星期,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而坏消息倒是一个又一个的接踵而来。
首先,是当地警局的警探来了一次家访。
撇开一堆例行公事的安慰和表示歉意的套话,其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我,事故发生的那一路段,附近刚好没有任何的摄像装置,而且警察在问了一圈之后,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目击证人可以给出有价值的口供。
所以警方对于这一起“hit_and_run”的交通意外,暂时没有什么可以跟进的线索。同时由于警力有限,只能姑且先把案子做归档搁置的处理。并向我保证如果发现了新的线索,侦破工作会继续展开。
对于这样的承诺,我只能说一句“呵呵”,其实它就相当于是变相地告诉我说,这案子没得查了,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算数。
因为事实上,这样的案子在洛杉矶并不少见。有许多类似的案子就在这样等待新线索中被人慢慢地遗忘。
我可以理解警员们的无奈。因为绝大多数时候,这都是在街上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没有规律可寻,也没有动机可挖。肇事者本身也不想意外发生的,只是一旦发生了,本能地选择了逃跑而已。对于警探来说,的确是属于很难破获的案子。
但这并不代表我就不感到气愤。因为,同时我更加清楚,我的这起案子之所以会被冷落,也是因为我这样的受害人实在是太普通了。假如现在出意外的是某某大明星,你猜这些警力有限的探员们会不会就此搁置案子呢?
当然不会了,只要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能给办案人员带来直接的好处,他们是一定会拿出愚公移山的劲头来解决这个案子的。而不会好象现在这样,只是做做官样文章,给受害者做完一份笔录之后,整个案子就算告一段落。至于所谓的以后,也再也不会有了。
但是,我的这个案子不一样。
我很肯定,这个撞了我的司机并不是出于意外,他是有意为之的!
我是被人迎面撞上的,谁能相信一个粗心的司机,会在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仍然能够那么平静地注视着即将被撞倒的人?我有足够的时间看到并且记清楚那张年轻的脸,我更相信他在那时候也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踩下刹车的。但是他没有。
我不知道那人是为了什么,想要故意撞我。我只知道,自从手术后醒来,有好多个夜晚,我都从噩梦中惊醒,最后停留在我记忆里的总是那一双冷静、漠然的眼睛。
我把我的猜测告诉警员,但是从他们敷衍的口吻里,我听得出,他们认为那只是创伤后遗症,只是我自己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而已。
这时候,我突然体会到了母亲当年的那种无助。那种明明自己说的都是真话,可别人就是不相信,还要用一种同情可怜的眼光来看自己。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意慢慢地浸透了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灵魂。
但是我不甘心。
于是,为了证明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在警员来访之后,画出了那个肇事司机的轮廓图,并请卡门帮忙送到了警局。
只可惜,警员在收下轮廓图时所说的会送去做面部匹配识别分析,最后也还是没有了下文。
同警方的不了了之正相反,医院的账单却是那么的真实。
回来没几天,医疗费用的明细也紧跟着寄了过来。从急救车到手术室再到医院病房,不同部门的单子一张张如雪花般飞来,每一笔支出用在什么地方,都写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就算知道得再清楚也没有用,因为那并不只是一个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的是一张张绿色的钞票。而我却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找这一笔计划外的开销。
本来在中介公司上班,那里倒也有一份统一的员工的医疗保险,虽然不是那么的好,但总归是聊胜于无。可是我已经被那里开掉,自然不能再享受他们的员工福利。而我自己,时间那么短,也还没来得及重新再去买一份保险。
现在肇事司机又完全没有着落,这所有的费用不全都落在了我自己头上吗?
何况,这些还不是全部。为了能够恢复双腿的知觉,主治医生还很尽责地给安排了一系列的物理治疗。而这些理疗项目,可不是说没见效就不收费的哦。再把这些一样样加起来,我觉得自己对着账单都要出幻觉了:那些数字就和出租车的计费表一样,会自己不断地往上跳。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才能从这个糟糕的境地里脱困出来。
撞我的人找不到,甚至办案的警察都已经放弃。
理疗做了几次,完全不见效果,可是账单还是一样要付的。
我一共就只有千把块钱的活期存款,又哪里够付医药费的十分之一?我又不希望接受卡门、路易斯的帮助,便是鲁文的钱,我也不想用,所以目前似乎就只有信用卡透支一条路可以走了。可是,透支的钱,到那一天才能还清呢?因为现在,就是连酒吧的工作泡汤了。
但是最坏的情况是,如果双腿继续没有只有知觉下去,我当记者的理想也即将付诸东流。而在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地方,还有一个想置我于死地的人在偷窥着我。
我知道我开始变得很得烦躁。成日里疑神疑鬼,为了一点点的小事,就大发脾气。而且每每总是歇斯底里地情绪失控。
我也想改变,只是我的自控能力变得非常薄弱。
不过短短一个月时间,鲁文终于感觉他受够了。
最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再是他认识、所爱的那个我。因此,他提出了分手,离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