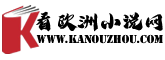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上官小侯爷!怎么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了啊?!莫不是怕了本王不成?”
函谷外,城墙下,呼韩邪氏仍恬不知耻地叫嚣着。
“呼韩邪氏!你这狗贼!太过狂妄!岂不知死字怎么个写法!”泽渊实在气不过,一口气跑到城墙上朝着城墙底下的呼韩邪氏谩骂着。
“叫上官小侯爷出来,怎的,他这般畏惧了?他自己不敢出来,竟叫你这小娃娃出来喊山门!”呼韩邪氏歪着头朝城墙之上的泽渊就是一顿讥讽。
“用不着我们侯爷,信不信小爷我就能徒手灭了你!”泽渊不甘示弱地回骂道。“不过是小爷的手下败将,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在这城墙之外嚷嚷,真不知羞!”
“本王不与你说,叫你们的上官小侯爷出来!”呼韩邪氏在函谷外稳坐马背之上托着下巴斜眯了泽渊一眼道。
“本侯出来又能如何?”
话间,上官瑾年淡然地走到城墙上,嘴角轻蔑一笑。
“我说上官小侯爷,不若你开城投降吧,也好免了本王这一厢苦苦鏖战。你说呢?”呼韩邪氏大手一揽道。“为着你上官小侯爷本王这些个豺狼奔波到了现在可各个都饥肠辘辘了。”
“呼韩邪氏,你以为,你还能得意到几时?”上官瑾年凝视着城墙下的呼韩邪氏,不免有些反感厌恶至极。
“得意不得意的,也不全然在于本王,也得看你上官小侯爷给不给本王这个面子和机会啊。”呼韩邪氏直了直身说道。“南国的将士们,你们听着!若你们开城投降!我呼韩邪氏定奉你们为坐上宾客!瞧瞧!你们昔日的檐穆小将军就知道本王此言绝非虚说!”
“是檐穆将军?!”
“真的是檐穆将军?!听闻昔日疆场之上檐穆将军早已战死,如今他怎么会投身于呼韩邪的帐下?!”
“果真是檐穆将军!他竟然还活着?!”
立于函谷城墙上的南国众将士一看到呼韩邪氏麾下的檐穆分分炸开了锅,各自议论纷纷。
“安静!”泽渊大手一挥道。“此乃呼韩邪氏那狗贼的离间之计,好蛊惑人心,让我们南国之师军心不稳!别自乱了阵脚!!”
“我不想死……我还有年迈的老母亲,她还在家中等我回去尽孝呢……我……我不要……”
人群之中,一人抖抖瑟瑟的扔掉了手里的长矛,只听得“扑通”一声,只见那人跪在了地上怅然掩面哭泣起来。
“我也不想死……我还没娶妻生子呢……我还有大好的年华……我……”
“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回去呢……我……我也不想死……”
硝烟四起的疆场之上,箭矢横飞的函谷墙头,南国的士卒们一个见一个地弃了兵器扔于地上。剩余的,只两眼空洞无神,似是早已麻木。
“捡起来!”泽渊一声呵斥道。
“我南国将士,皆为一身肝胆的好儿郎,不是么。”上官瑾年环顾四周,扫视了众将士一番道。“我们因何而战,不就是为了我们身后的这片南国之土么?在这片土地上,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爱的人,为了这个,所以我们才站在这里,我们不惧死的危险,只为了好好守护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安乐无虞的生活,不是么……”
“你们还不明白么……没人愿意打这场仗,谁都想太太平平地过安生日子,都是他呼韩邪氏逼我们的,我们不得不站在这里与他们生死相搏,如若我们听他们所言,开城投降,试问,他呼韩邪氏真就会如他所言奉你们为上宾?”泽渊慷慨激昂的发自肺腑道。“会不会奉你们为上宾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旦开城投降,我南国边防从此失守,呼韩邪氏那狗贼必定会长驱直入,血洗我南国之城,肆意屠戮残害我南国百姓!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忠孝仁义么?!”
“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开城投降!”
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下,人群中似是有人发出了正义之声。
“对!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开城投降!”
“绝不开城投降!绝不!”
渐渐的,低弱的士气在一番鼓舞之下,宛若重燃的烈焰,又恢复了其熊熊的气势。
“敬酒不吃,吃罚酒!”
呼韩邪氏眼见自己棋差一招,计划败露,只得气的暗自跺脚。“本王的好驸马,好军师,现在,该是你为本王建功立勋的时候了。”
“我……”
檐穆到底还是被呼韩邪氏当做挡箭牌一般,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去,则为本王建功立业,本王看在你这般忠心耿耿护主的份上,自然是不会亏待了你去,如果不去,我想,你知道你不去的后果会是什么的吧……”呼韩邪氏斜眯着眼打量着身旁的檐穆威胁道。“别忘了,镜屏现下有孕在身,你也不希望她腹中的孩子一出世便没了父亲吧……”
“我去就是了……”
敌不过呼韩邪氏的威逼利诱,檐穆只得硬着头皮一人轻骑走了出去。
“瑾年!”檐穆昂着头朝城墙喊到。“开城投降吧!我保证,呼韩邪不会亏待你们的!更不会血洗函谷屠戮百姓的!”
“檐穆!你还敢有脸来!你口口声声说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上官瑾年一见到檐穆就痛心疾首的呵斥道。“拿你昔日作为我南国的英雄那一世英名保证,还是拿你如今这徒有的呼韩邪氏驸马的虚名保证?!”
“我!!……”檐穆将脸垂丧着耷拉了下来。
是啊,现在的自己,到底算个什么,活人?还是死人……
现在的自己,又有什么面目站在这怏怏的函谷城下……
现在的自己,更有什么资格,以呼韩邪氏驸马的身份,做这多行不义必自毙之事……
“檐穆!你我二人,早已割袍断义!我上官瑾年那日亦曾对你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我二人,若有再见之时!则为敌人!我上官瑾年定会对你刀剑相向!”上官瑾年凝视着城墙下的檐穆揪着心痛斥道。“你若不想死,就给本侯滚!你若还为呼韩邪氏那狗贼卖命!别怪我上官瑾年不念昔日的情分!更别怪我刀剑无眼!”
“我……”
檐穆又再次垂下了头,今时今日,也许,若有个不测,死在了上官瑾年的手里,也好……
自己死了对自己而言反倒是个解脱。
“不!!!!”
众人对峙之时,只见得呼韩邪镜屏一人轻骑跑来了这疆场之上。
“娘子!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去!!”檐穆见呼韩邪镜屏往函谷本来忙扯着嗓子嘶吼道。
“镜屏!快回去!!”一旁的呼韩邪氏似是也发现了呼韩邪镜屏的举动一般,忙转过身来呵斥道。
“吁——”
只见得呼韩邪镜屏稳坐马背之上,停在了两军阵前,与檐穆隔开不过几步之遥的距离。
“哥哥!停手吧!不要再打了!!不要再造杀戮了!!就当为我腹中的孩子积点德吧!”呼韩邪镜屏朝着呼韩邪央求道。
“胡闹!女儿家家的!你懂个甚!快回去!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呼韩邪氏不予理会的呵斥道。
“镜屏是不懂,可我知道,不管是南国人,还是我们番邦人,都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哥哥,收手吧,我们回去,回去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呼韩邪镜屏眼里噙满了泪道。
“妇人之仁!来人!把镜屏公主带回去!”呼韩邪氏大手一挥叱令道。
“我看谁敢!谁若动我分毫!我必血洒当场!!”
只见得呼韩邪镜屏不知何时,竟从袖口取出了一柄匕首出来,架于自己的颈侧之间,牵制着呼韩邪氏。
“你想干什么?!别乱来!”
似是被呼韩邪镜屏唬住了一样,呼韩邪氏顿时愣住了阵脚。
“城墙之上,可是上官小侯爷?!”呼韩邪镜屏对着函谷城喊到。
“正是本侯!你是镜屏公主吧!”上官瑾年打量着呼韩邪镜屏道。
“我是呼韩邪镜屏,上官小侯爷的英名,我曾听夫君檐穆有所提及,今日有缘一见,侯爷之名,果然名不虚传!只是镜屏无缘结交侯爷这等英雄豪杰!”呼韩邪镜屏言辞恳切的说道。
“镜屏公主严重了,本侯不过区区一介武夫而已,担不得那般子的虚名,不像你夫君檐穆那般担的心安理得!”上官瑾年蔑视了檐穆一眼道。
“上官小侯爷误会了!昔日在疆场上救下夫君的人是我!求着夫君留下来的人亦是我呼韩邪镜屏,我夫君仁爱,拗不过我!这才留在了我这!并不是他不回南国,而是因为我这腹中已有了他的骨肉,如此才……”呼韩邪镜屏朝着上官瑾年解释道。
“不管如何!他檐穆,确是投敌叛国了!本侯只好清理门户!此事!不关镜屏公主的事!还望镜屏公主不要插手才是!”上官瑾年不得不狠下心来叱道。
“不!檐穆是我的夫君!他的死活!我必须管!”呼韩邪镜屏执拗道。
“来人放箭!射死这个南蛮子!”呼韩邪氏一声令下,麾下的弓箭手正严阵以待,蓄势待发。
而函谷城上,上官瑾年亦张拉着弓箭蓄势待发。
“不!!!!”
说时迟那时快,万箭齐发之时,呼韩邪镜屏眼疾手快的扑向檐穆,死死地挡在了檐穆身上!
“不!!!!!”檐穆翻过呼韩邪镜屏的身子,紧紧的拥在怀里。
“夫君……”呼韩邪镜屏撑着力气细细抚摸着檐穆的脸庞。
“娘子……你何苦……你怎么这么傻……”
檐穆将呼韩邪镜屏搂于怀里抱的更紧了,他将自己的脸紧贴着呼韩邪镜屏的脸,仿佛在把自己身体的温热之气过渡到呼韩邪镜屏的身上。
“夫君……对不起啊……若不是昔年的一面之缘,我也不会困你到现在……我的夫君……”呼韩邪镜屏瑟瑟依偎在檐穆的怀里,口中吐出的鲜血瞬时染透了身上的衣物。
“别说了……别说了……我带你回去……你会没事的……我找大夫救你啊……”檐穆紧紧搂着呼韩邪镜屏颤抖着道。
“来不及了……我的夫君,生的这般好看,叫我怎么也看不够……”呼韩邪镜屏细细抚摸着檐穆的脸庞,呢喃的语气渐渐变弱。
“别说了……我带你走啊……去什么地方都好……只是,你不要离开我啊……不要……”
檐穆紧握着呼韩邪镜屏的双手不停的哈着气,却丝毫不起作用。
“没用的……哥哥……不要再打了……到此为止吧……”呼韩邪镜屏望了望呼韩邪氏又摸了摸自己腹部泣道。“只可惜,这个孩子……不能出世了……不然,即使我不在了,有这个孩子陪着你……那该有多好……”
“不中用的人,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呼韩邪氏见此只大袖一挥背过了身去。
“你别睡……别睡……别睡!!我答应过你的,要去游山玩水的……你只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要如何!!”望着呼韩邪镜屏渐熄渐弱的气息,檐穆似是发了疯一般吼道。
“夫君……你……再唤我一声娘子……可好……”
呼韩邪镜屏强睁着眼,抚摸着檐穆的眼眸,撑着最后一口气恋恋不舍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她最割舍不下的男人,最终,呼韩邪镜屏的手从檐穆脸上渐渐滑落,到底还是撒手人寰了。
“娘子……娘子……”
檐穆紧搂着呼韩邪镜屏的尸身,空坐在地上,失了魂般喃喃自语道。
霎时间,只见得呼韩邪镜屏阖上的眼眸处似是有一滴泪垂落,许是她听到了檐穆的这一声呼唤吧……
“娘子……我带你走,我们离开这,什么尔虞我诈,什么你死我活,这些,我通通不管,我带你走啊……”
斜阳下,檐穆抱起呼韩邪镜屏的尸身,一人轻骑,缓缓策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