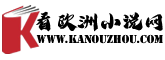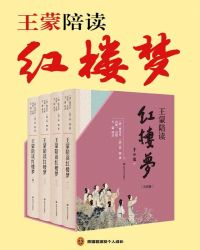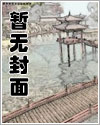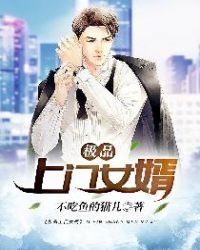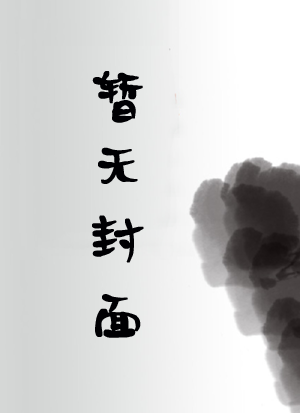快读《红楼梦》王蒙评(代跋)
快读《红楼梦》王蒙评(代跋)
冯其庸
在十年前(1986)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清代《红楼梦》评点派的文章,题为《重议评点派》,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一期。同时我又辑录了清代八家著名《红楼梦》评点派的全部评语,以程甲本为底本,依原评位置排印,书名为《八家评批红楼梦》,于199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重议评点派》就是该书的序言。
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重新评价清代的红学评点派,应该肯定他们的研究成果;(二)具体地列举了红学研究中十一个重大专题,都是评点派早已研究并提出了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看法;(三)我指出评点是传统的文艺批评方式,这种方式是可取的,行之有效的。有些人评点得不好,并不是这种方式不好,而是评点的人本身水平的问题。最后我呼吁说:
我敢断言,现在如果有哪一位红学大家,他确实具有很高的鉴赏力和很高的文字功夫,他对《红楼梦》具备了批评的条件,如果能由他来评批一部《红楼梦》,那么,这部《红楼梦》肯定会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
现在,十年过去了,果如我所言,由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兼红学家王蒙来完成了这样一件当代红学史上的大事。
事情是突如其来的:王蒙评点《红楼梦》我事先并不了解,直到拿到了书,才惊喜参半地翻阅起来。翻着翻着,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写文章介绍,因为它给了我冲动,它让我读后睡不着觉,我为它半夜里又从床上爬起来,觉得这篇文章非写不可,不写我的内心就不会得到安静。
我为什么在题上加“快读”两字呢?这倒不是叫大家快点读,虽然可包含这个意思在内。我这个“快”字,是痛快、解气、够味的意思。我敢说,读这个王评本《红楼梦》是真痛快,真够味的!真可以说“一下子被他抓着了,半世让你说不得”!
首先让我拍案叫绝的是王蒙为评点本写的“序”。大家知道,在清代最有名的《红楼梦》“序”要数戚蓼生的那一篇了,总共只有四百六十七个字,却让你回味无穷,真是“万千领悟便是无数慈航矣”!自乾隆以来,可以说至今没有一篇序文及得上它。有之,则就要数王蒙这篇了。
王蒙的这篇序一共只有一千五百字左右,比戚序多出两倍,但在当代的序文中要算是最短最短的了。
王蒙说:“《红楼梦》是经验的结晶。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红楼梦》就是人生。《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最后两句是警句。按评点派的办法,应该加密圈密点。真是“一下子被他抓着了”!“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这句话别人没有说过,是王蒙第一次说的。夫人生最长不过百岁,一般活到七八十岁也就可以了。可是到七八十岁时回顾往事,觉得有多少事想重新再来一遍啊!有多少事感到当时没有经验啊!但还真能再来一遍吗?逝水年华,是不可再来的。想再来一遍吗?那么就请读《红楼梦》吧!你可以随着他们从儿时到成年,随着他们去经历经历。我曾多次说过,《红楼梦》要曾经翻过筋斗的人来读,才会领会深切。感谢一场“文化大革命”,让当时所有的成年人都把筋头翻了个够。有的是彻底打倒,随时被批斗,这是正翻;有的是将别人彻底打倒,自己高举造反大旗,但到头来也被人们彻底看透了,这是负翻;还有的是钻头觅缝,拉关系,往上往里靠,终于达到了目的,但终于也被人们彻底看透了,这叫作侧翻……总之,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人们火辣辣地活过了一次,增加了不少生活的回味。有了这个生活底子再来读《红楼梦》确实是增加了“万千领悟”,但论语言,总是比不过王蒙的“等于活了一次”!多精辟的思想,多精警的语言!
王蒙说:“《红楼梦》是一部令人解脱的书。万事都经历了,便只有大怜悯大淡漠大欢喜大虚空。便只有无。所有的有都像是谵妄直至欺骗,而只有无最实在。便不再有或不再那么计较那些小渺的红尘琐事。便活得稍稍潇洒了——当然也是悲凉了些。”
“《红楼梦》是一部令人解脱的书。”这话过去有人讲过,也有人批评过,但经过“文革”这一场大波澜后,再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应该看得深一些了。我们从“文革”中看到了从有到无,也看到了从无到有,甚至于再从有到无。这样的变化,能不发人深思吗?能不想到《红楼梦》吗?或者读《红楼梦》时能不想到这种变化吗?《红楼梦》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悲歌,多么富有历史的深度啊!
王蒙说:“《红楼梦》是一部执着的书。它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疯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为了活而死是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
“《红楼梦》是一部执着的书。”这话,更抓住了《红楼梦》的根本。从根本上来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一把辛酸泪”,才是作者的心声。《红楼梦》是写到了无,写到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红楼梦》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这无,而是它对人生的执着,对爱情的执着,对是非的执着,对现实的执着……一句话,对自己个性的执着,对自己理想的执着。因为执着,宝玉几乎被打死;因为执着,可以不理睬仕途经济;因为执着,可以非圣贤而谤僧道;因为执着,宁要木石前盟而不要金玉良缘。清代的评论家徐瀛说:
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公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谈笑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
西园主人评林黛玉说:
盖以儿女之私,此情只堪自知,不可以告人,并不可以告爱我之人。凭天付予,合则生,不合则死也。故闻侍书之传言则绝粒,听傻大姐之苦诉则焚稿,私愿不遂,死而后已。此身干净,抱璞自完。……
这是对贾宝玉、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的最深刻的理解,这也是对《红楼梦》、对曹雪芹的执着的最好的解释。阅古今之书,写男女之情而能至于林黛玉、贾宝玉这样的执着深刻,却是古今少有。王蒙说:“它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疯的事情。”这话说得多好!正是因为有这一点坚定的信心,所以人才活得有意思,有目的,有滋味!人归根结底并不是专门为着活着而活着的,也不是专门为别人的需要而活着的。人应该为这真正的活着而活着,为着人的尊严,为着自己的崇高理想,为着自己的真感情、真思想,真喜、怒、哀、乐,真个性而活着。如果没有了这些,活着的人也不过是一个活的人体模型。读《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有时让你笑,有时又让你为之癫狂,就是因为他们是两个有美好理想的典型,是两个执着的典型。
王蒙说:“读一次《红楼梦》,又等于让你年轻了二十年。”这话实在是读《红楼梦》而能深入肌理之言。
王蒙说:“你会觉得:不可能是任何个人写出了《红楼梦》。”“是那冥冥中的伟大写了《红楼梦》。假曹雪芹之手写出了它。”“《红楼梦》是一部文化的书。它似乎已经把汉语汉字汉文学的可能性用尽了,把我们的文化写完了。”我国本来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说法,它被王蒙巧妙地用到赞《红楼梦》上来,真是高明之极,比起那些死乞白赖地要把《红楼梦》说成是自己的什么人写出来的人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岂止上下床之别而已。
我常常觉得我最幸福的是一个中国人。又认得汉字,又读过一些古书,特别是读了好多遍《红楼梦》,还在“文革”的大动乱中用毛笔偷偷地抄了一部庚辰本《红楼梦》。特别是还亲身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看到了自有历史以来的一次大波澜,也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读了一部历史!
我觉得中国的文字实在美妙极了,《西厢记》《牡丹亭》已令人口齿生香,到了《红楼梦》,文字的精妙,语言容量之深度,表情达意之曲折入微,实在是说部第一。王蒙对中国文字的热爱和高度评价,真是说到了我的心里。记得前几年,徐朔方教授有一篇关于中国文字的好文章,精警至极!我读后多年来一直中心藏之。须知中国的文字是值得我们生死系之的啊!
王蒙说:“你和《红楼梦》较劲吧,你永远不可能征服它,它却强大得可以占领你的一生。”这话说得多深刻啊!1986年我在哈尔滨《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题过一首诗,诗云:“大哉红楼梦,浩荡若巨川。众贤欣毕集,再论一千年!”1994年6月,我在台北参加甲戌《红楼梦》研讨会,和周策纵先生韵再题云:“故国红楼到海边,论红何止一千年。人书俱老天难老,更有佳章待后贤!”我的意思与王蒙的意思完全一样,但王蒙说得直截,说得现代化,说得容易叫人理解。如果一代代的每个“红迷”的一辈子都被《红楼梦》占领了,那么它的占领何止一千年呢?王蒙说得真是深刻而巧妙。
在王蒙这篇序里,像上面这样的精警的段落、句子,几乎通篇皆是。可以说从头一句起,就让你不能放下,必须读下去。《红楼梦》也真幸福,前有戚蓼生的“序”,可以作为有清一代的代表;后有王蒙的“序”,可以作为我们时代读《红楼梦》的代表。所以,曹雪芹似乎也可以减轻一些他的“谁解其中味”的慨叹了!
王蒙对《红楼梦》所作的评语,也可以说随处散发着理解的智慧和意趣。他对《红楼梦》的理解是深刻的广博的,他对曹雪芹的屈原式和司马迁式的胸怀,以及他的忧愁、多感、深沉和生死系之的真情是有相通之处的。他的评,是一个大才子的评,是一个大作家的评,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大文化人的评。对《红楼梦》的评,已经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了,现在忽然出来了一位大评家,出版了一部评点本的《红楼梦》,这不能不说是“红坛”的一件大事和盛事!我曾经说过,有了《文心雕龙》以前的优秀的文学名著,才能有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我们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它也在创造和培育着自己的知音。有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历史必然会创造出能理解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和呼唤,终究会唤出能解其中味的人的!我们时代第一部王评《红楼梦》,就是这种标志和象征。当然,当代的和以往的红学家、《红楼梦》评点家、《红楼梦》的痴迷者,其中也不乏堪称解味或部分解味的人,但以评点派的形式出现的,王蒙是当代第一人。同时,我个人还觉得他是解味较深和较多的一人!如果要想找出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全都理解曹雪芹,把曹雪芹的学问和心意思想搞个底朝天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曹雪芹毕竟是旷古未有的奇才,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生活不同了,思想方式不同了!
我读王蒙的“序”,为之中夜不寐。我读王蒙的评语,时时为之击节,为之连连浮白,为之唏嘘叹息,为之大欢大乐,也不免为之黯然神伤和凄然泪下,我几乎分不清是被曹雪芹感动,被续作者感动,还是被王蒙所感动了。
一部《红楼梦》,王蒙的评是那么多,不要说是一言难尽,就是万言也难尽的。我这里就拣几段重要情节的评,作些引录,至于要深入而全面了解品味他的评,那我的引录和介绍是无济于事的,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尝鼎一脔罢了。
以下我就以情节的先后,对评语略作引录:
在第一回开头,王评说:
既为梦幻,何真事之有?“曾历……”“故隐……”可见所历是真,非梦,但最后又确是一番梦幻,至少感到是梦了。梦耶?真耶?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也是文学的根本问题。无真无文字,无梦行吗?
在第一回赤霞宫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的神话故事上,王评云:
一个绝妙的爱情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却又是现实故事的升华。
是悲哀的爱情故事的飞升。
这个故事统御着宝黛爱情故事的全过程。
令人神往。令人能不泪下!
在第四回正文前评云:
毛泽东氏倡第四回是总纲说,他是作为革命家、政治家,把“红”定性为“政治小说”,把“红”的内容定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兴衰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探讨的。当然四回极重要,四回确实讲到了“四大家族”,言之有理。如果从哲理上掌握,还是第一回开宗明义。
从爱情、从十二钗的命运及整个人物的命运来看呢,总纲却是下一章了。一般红学家最重视、最花力气破译的也是第五回。
“总纲”多了,还算不算总纲呢?
麻烦就麻烦在“红”这部书太立体,太“多元”了。谁又能一以制之呢。
在第五回开头综述往事这一段,王评云:
这段综述。一般地技巧地说,本为小说家所忌,盖综合判断跑到了叙述描写、情节展开的前面去了,概念走到了艺术表现的前面,作者先期把结论捅给了读者。
然而,大师、巨著,自有不计小节处,由于有真情实感真生活真学问,由于有无数活生生的东西即将表现出来,技巧不再重要,技巧上的失策仍更是不拘一格,化腐朽为神奇。而缺少总体价值的三流作家三流作品,即使手法讲究,也只是化神奇为腐朽。大师就是大师,不服不行。
在第三十三回贾政打宝玉一段,王评云:
曹雪芹写大场面,如指挥一个交响乐队,贾政如何,贾环如何,宝玉如何,小厮如何,清客如何,聋婆子如何,王夫人如何,李纨如何……有条不紊,错落有致,合成一个亦喜亦悲亦闹亦正的大交响乐。
在贾母在“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以下一大段。王评云:
语出不凡,先声夺人,一语穿透多少屏障!贾母岂是等闲之辈!
在贾母“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附,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一段旁,王评云:
一句一刀,刺刀见红,字字出血!
在贾母直言“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数语旁批云:
对答如流,批深批透,贾宝玉体无完肤,贾政亦体无完肤矣。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各有其悲。
在三十三回末尾宝玉挨打后抬进房里一段,王评云:
这是前四十回的一大高潮。
这一高潮涉及许多人和事,许多矛盾侧面。
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要大闹大乱一次。
每个人的表现都恰如其分,恰有其理。忠顺府长府官话说得并无差错,贾政怒得更有道理,也是一身正气。贾环进谗不佳,毕竟无风不起浪。贾政打得有理。王夫人说得有理。李纨哭得有理。贾母气得骂得赖得有理。凤姐料理得有理。袭人查核得有理。这一切矛盾又都成了以后的矛盾发展的预伏。
真大手笔也!
在三十五回开头“这里林黛玉还是立于花阴之下,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一大段旁,王评云:
黛玉立在花阴之下,看一批批人看望宝玉,这个角度选得极佳。突出了宝黛二人处境之大不同,更突出了黛玉与这个家族的疏离感。情也是负担,是沉重的包袱。黛玉反不能随随便便与别人一起去怡红院“打花胡哨”。
在黛玉进院进屋子后,“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这一大段文字后,王评云:
林黛玉的这种敏感清雅的独处生活方式,使评点者不伦不类地联想起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她完成学业后几乎是足不出户。她写诗,完全不是为了发表,她很短命,温柔纤细,死后才成为著名诗人。
《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也是长期过着封闭的生活的。
林黛玉的特点其实适合搞艺术,她是艺术型人物。她与狄金森相比,最不幸之处是她并不能真正与世隔绝,相反,她处于关系复杂,一个个纵横捭阖、钩心斗角的贾府的矛盾中,她与宝玉的感情甚至把她也推到了矛盾旋涡的中心,她成了矛盾一方,孤立无援必败的一方。而且,她生活在一个视文学艺术为下流异端的社会里。
在三十八回吃螃蟹的一段,王评云:
吃螃蟹一节,确实可以当作风俗画来看,作者写得有鼻子有眼,实实在在,方方面面,严丝合缝。这是求实求真的一套笔墨,阅读效果是感同身受,使你忘了是小说。
好小说既是小说,又常常不是小说。是小说,使你惊叹于小说家的想象力、才华和博大精深,直至匠心独运。不是小说,使你见到感到了时代、历史、人生、宇宙,至少是生活的图画。
在黛玉咏螃蟹诗的一段,王评云:
这是大观园的一幅行乐图。简直是天堂,是活神仙的日子。有美景,有美食,有美文(诗)更有美人,几乎人人开心,个个高兴。几近于一次联欢节,狂欢节,诗歌艺术节,美食节,菊花节。节日般的快乐一去不再,永远难忘。即使重返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重新永远永远地复归为一块石头,想起这次吃螃蟹咏菊,能不依依?
乐哉人生,哀哉人生!《红楼梦》请君尝尽人生滋味!
在五十回争联即景诗的一段,王评云:
这是大观园的诗歌艺术节或青年联欢节。也可以叫白雪节。
这是一个高潮,一个青春、才华、欢乐的高潮。包括“时装表演”,野餐烤肉,联诗。诗可以“兴、观、群、怨”,也可以玩耍,比赛,尽情发挥。
这会留下永远的美好记忆。
此后虽仍有游乐,却再也没有这种规模了。
在五十一回月夜晴雯只穿着小袄出去吓麝月一段,王评云:
袭人不在,诸事略显蹊跷。
天冷、夜长。晴雯与麝月侍候宝玉入眠。夜半起来漱口喝茶。麝月出去,晴雯要唬她,受惊……云云,都是鸡毛蒜皮,平凡的琐事。
这些琐事的后面,有一种与白天的红火热闹纠缠赖皮完全不同的气象,给你以且惊且疑且闷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好像你也与他们共度了有事无事、无事有事、冷气逼人的一夜。你感到了生命的孤单和脆弱。
你有一种风雨飘摇的预感。
而这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雪芹真巨匠也。这样的笔墨,活似来自天授。
在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演《西楼·楼会》一出时,王评云:
一面是华丽雍容,庄严肃穆,一丝不苟,煞有介事,冠冕堂皇,排场讲究。一面是腐烂颓败,势孤力单,蝇营狗苟,鬼鬼祟祟,捉襟见肘,于是华丽中见空洞,庄严中见虚伪,严格中见呆木,堂皇中显露出无可挽回的颓势来。
一支笔,既写了大面上的良辰美景气势煊赫,又顺手一击,暴露出了里子上的烂洞。
内里空了烂了,只剩下了表面的行礼如仪。
在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中,王熙凤说到“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时,王评云:
“散了吧,散了吧”的声音,从此不绝于篇。
接着在园子里大放烟火,贾母说“夜长,不觉得有些饿了”,凤姐忙回说“有预备的鸭子肉粥”一段,王评云:
消寒消夜,快乐中令人感到疲倦乃至清冷。
特别是凤姐的“笑话”,欲笑不能,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狐疑,令人不安。若有深意,文章后面似又有文章。
“红”书整个写得相当实在,过年、过元宵节诸事历历在目。但作者没有忘记非纪实的玄虚手段。
在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赵姨娘当着李纨的面羞辱探春时,王评云:
读“红”,常常觉得赵姨娘的形象不够立体丰满,甚至觉得曹公对这个人物有成见,把她漫画化了,厌恶之情溢于笔端,没有深度。何至于一张口一举手便觉得傻鄙陋至此!
只是近一两年,这种想法略有变化。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人,生活就是这样的啊!
在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段王评云:
这一个光明单纯青春的镜头照出了所有的“红楼梦女子”的可怜,也照出了此后湘云自己的命运的可怜。
这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是如诗如梦的刹那高峰体验,这是空谷足音,这是人生本来应该过得如何自由而且快乐的转瞬即逝的“闪过”。
从此,一去不复返矣!哀哉!
在“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这一大段旁,王评云:
一副自然之子、光明之子的形象。
女孩子本来是天生光明纯美的,却封闭在那样一个外面光里面烂的环境之中,只是在醉卧以后,极其偶然地昙花般地一现自由人的光辉。
这样的女孩子却要被一再荼毒下去,令人怎生不慨叹。
在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钗抓签一段,王评云:
反映了宝玉也反映了作者对钗、黛的选择上的困惑,乃至遗憾。似钗似黛(见第五回)才算“兼美”。
对于黛玉的定情,并不妨碍对于宝钗的高度评价、艳羡。
宝钗毕竟也是一种极致,一种理想,正像黛玉是另一种。
作者理想的女性似应是二者的兼美,实际上又做不到,实际上常常是顾此失彼,重此轻彼。
作者钟爱的女性当然是黛玉。
作者钦佩的女性却是宝钗。
在芳官唱了一支〔赏花时〕“翠凤翎毛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探春又抽了“日边红杏倚云栽”的签的一段,王评云:
是酒令,是花名,也是一些朦朦胧胧的诗句。
是花,是诗,是谜,是象征。
狂欢中不无凄凉:任是无情,红杏倚云,深夜花睡,花了送春,莫怨东风,又见一春,低吟短唱,余音绕梁,谁能解破,谁能自已?
在黛玉“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花,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道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一段上,王评云:
这才是小说,高明的小说。
宝玉情感,或有专注,二人丽质,难分轩轾。宝玉的情感,又明白又不明白,又掰得开又掰不开,又专一又不那么专一,呜呼,此为小说笔墨也。
如果把其中一个看成“第三者插足”,看成阴谋家、坏蛋,那种人物、故事,与“红”首回便嘲笑的三流传奇又有什么两样?
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抄检到探春房里,王善保家的“便要趁势作脸,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地笑着说“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一段,王评云:
探春一个耳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三百年不绝!
即使大势已去,也不能让恶人毫无忌惮。
整个“红”,黏黏乎乎,纷纷乱乱,如麻如粥,此一耳光,却有英勇豪迈气概,金声玉振,大快人心!
这一及时起板,大灭了小人的威风,大长了好人的志气。
王善保家的之类的家伙呀,你们不注意维护一下自己的嘴巴吗?
在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妙玉最后完成联句后,王评云:
可以以本回写笛声的一些话头形容这一回文字。
搜检时波谲云诡,铙钹齐鸣;到此节,万念俱寂,一片空明,只剩下一件乐器的独奏。
舞台转换,角色转换,布景与灯光、效果皆别一个天地矣。于是黛玉湘云,尤其是妙玉,成了主角。
一个美貌的带发修行的才女——尼姑,提笔完成了联诗,而且说到气数。你不能不怵然、嘿然吗?
读后夜风月色,滞留心中,难以忘怀。
在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晴雯死后,宝玉听了丫头讲晴雯不是死,而是上天去当花神,专管芙蓉花这一段,王评云:
此节小丫头谎言极有味道。
对于小丫头来说,纯粹信口开河,是假。对于宝玉来说,恰合他的幻想、愿望、思路,他对于这个谎言的充分相信,是真。
当人们对待真实毫无办法的时候,幻想便会应运而生。不能没有幻想。
当真实与人们背道而驰的时候,幻想表现着人,幻想就是人,而文学常常就包含着这样的幻想。美是幻想。美是纪念。美是“自欺欺人”。
小丫头在进行着文学创作,她的创作受到了美的接受者贾宝玉的激赏,因为她的创作符合宝玉的美学理想、美学规范,而且包含童心。
这是幻想的美,文学的美。这又是幻想的可怜,文学的可怜,美的可悲可怜乃至可笑!
读了这一段,哭乎?笑乎?叹乎?嘲乎?摇头乎?惋惜乎?反正更加令人惆怅。
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曹雪芹的笔当真成了精了!
对《芙蓉诔》,王评云:
贾宝玉——其实也是曹雪芹,确实以极大的篇幅,以极丰富的词汇,以极丰赡的形式,下了功夫写这篇诔文。
由此可见他——他对于晴雯这一人物的重视,对于晴雯之死这一事件的重视。“规格”是超一流的。
曹公本身亦有一种抑郁不平之气,假悼晴雯之诔以发之。一股未尽其才之怨,假此诔以展之。
在七十九回贾宝玉、林黛玉改《芙蓉诔》一段,王评云:
搜检大观园,从精神上说(即不是从考据上说),乃是曹氏“红”著的结束。
具体的终结,应是终结在《芙蓉诔》上。以洋洋洒洒、规模宏大的芙蓉诔,以聪明美丽的晴雯的奇冤至死来结束曹氏“红”著,宜哉!晴雯之死,是搜检的最直接最严重最可悲的结果,是前八十回悲剧的顶峰,是事实上的对于王夫人——袭人(恰恰不是凤姐)的仁义道德直至权力运作(包括奴才们对于这种权力的投靠、适应、效忠)的控诉批判。
在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黛玉焚稿的一段,王评云:
黛玉将死,要毁掉她与宝玉的情感的一切痕迹。毁掉她自己的青春、生命的一切痕迹。
这些举动,表达了她深切的绝望与痛苦,客观上,也是对人生的抗议。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算什么!爱算什么!青春算什么!以死相争!首先从精神上自杀干净,再从肉体上闭眼。撒手而去。
同回在宝玉完婚一段,王评云:
宝玉“完婚”,真是天下奇事。奇闻。奇文。“红”真是奇书。
人生多误区!本以为走入这一间房子,却走入那一间房子去了。
婚姻离奇,凤姐离奇,薛宝钗更加离奇。她对这种“神出鬼没”的做法怎么毫无反应?连些微的疑惑、烦乱也没有?
事奇理不奇,自以为天从人愿得到了黛玉,揭开盖头却是宝钗,而黛玉已经一命呜呼。追求A,得到B,毁了A,这样的事固不止宝玉碰见也。
后四十回诸多瑕疵,但还是被广泛接受,与这些关键段落写得好有关系。
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正文前,王评云:
魂归离恨天,泪洒相思地,此两句已脍炙人口矣!
读之怆然泪下。语言的力量是难以转述的。
此回回目极佳。特别是联系到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令人神伤!
在黛玉气绝的一段,王评云:
死,总有一死。
可悲在于临死不得交通,隔膜着,怨恨着,遗憾着。
这样的人生的终结,便只有痛苦了。
这样的痛苦,又何必生?天乎!天乎!
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提心”中,李十儿向贾政叙说“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一段,王评云:
正面写大观园之外乃至京都之外的吏治官情,除此回是绝无仅有的。这是续作的一个突破。
贪赃枉法有理,清廉没门儿,风气已经如此,实际利害关系已经这样构筑起来,任何人都没有回天之力。
而且贾政并不清楚,他不是也参与了“营救薛蟠”的事了么?
贾政又不了解下情,没有一套应付对策,怎能不落个虚张声势,徒落笑柄的下场?
第一百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骢马使弹劾平安州”,贾府被抄家后,王评云: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可将此前书中所写的一切,看作此回的准备铺垫。
一步一步,一站一站,终于走到了这一站:这是“红”的条条道路通向的“罗马”。
虽然紧紧勒住了“缰绳”,这一回仍然是惊心动魄!
读之心惊肉跳。
人皆有不忍之心,读了一百多回了,对贾府也有了点感情了,虽知其黑暗,知道其必败应败——恶贯终将满盈,读到这里,仍然难过。
多少经验,多少教训,多少痛苦,多少血泪!谁能学得更聪明些呢?
在第一百七回“散余资贾母明大义,复世职政老沐天恩”中贾母散资后,王评云:
此前的贾母,一直是一个会享福,专门享福的老太太。
恰恰在抄家的大考验中,表现出贾母的另一面,她也会“度灾”。她周到,大气,不怨天尤人,不惊慌失措,不迁怒旁人,所言、所行、所思,老练、诚恳、全面。她不愧是见过世面的有经验的“老祖宗”,她表现了“帅才”。儿孙辈能不愧死!
在后四十回,性格大大焕发了光彩的是贾母。
在第一百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中,宝玉考毕出场而失踪一段,王评云:
对宝玉中举后出走的设计,“红学”家颇多诟病,认为是俗,是脱裤子放屁……得失难较。首先,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与讽刺。从贾政到袭人,一直对宝玉谆谆教导,要取功名。偏偏他完成了功名的任务后走了。其次,他如何能离开贾府,离开那种众星捧月式的包围呢?入考场最天经地义。入考场的结果不是得中荣归,而是中而后走。又是一种翻案的惊人之笔。再者,如果黛玉前脚死宝玉后脚走,反倒没有戏了。现写宝玉为黛玉之死而极端痛苦,而得了精神病,之后,是整个一个过程,与宝钗亦可相处居室了,袭人也俨然屋里人地教育上来了,他经历了家族的衰微,他经历了自己的小家的初步稳定,他像个傻子一样地接受上下左右的教导督促,他再次游历了太虚幻境,他经历了波涛起伏终于平静的精神旅程,最后,他又玩了一下功名,逢场做戏地考了个举人,该体验的他全部体验完了,不去做和尚,也就只有去自杀了。
但是不,他还有一条出路,把这一切写下来。以出家和自杀的决心写下一部小说来!
在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中,贾政来信,告知宝玉已成佛的消息后,王评云:
红尘福分,宝玉比任何人都多。
宠爱、地位、条件、服务,都是不可思议的最高级别的。
尤其是,他处于那么多女孩子的宠爱之下,他爱了那么多女(还有男)孩子,又那样深情地专一地爱上了黛玉。古往今来的读者,谁能不羡慕他的生活与环境?
这种福太多了。终于,混推混搡,更生厌烦了。他的人格,他的感情遭到了蹂躏、欺骗、歪曲、压制、漠视。更是由于有福,他才不那么满足于能生存能吃喝能从异性身上满足生理欲望,他才绝望。
这是一部绝望的书。这是一部控诉的书。这是一部无可如何的书。
在同回贾雨村重逢甄士隐追怀往昔的一段,王评云:
一个爱情悲剧与家族衰落败亡的故事。
把这样的故事推到尽头,便进入了生命发生、生命意义、爱情发生、爱情命运领域。进入了终极领域。
在这个领域,你见到了原生的大自然,女娲补过的天,你见到了一块石头——晶莹的宝玉——情迷而后豁悟,生活在温柔富贵乡而终于弃绝了温柔宝贵的贾宝玉——和尚——被和尚道士带走的宝玉——石头——大自然。
这是宝玉的故事,生命的故事,爱情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地球的故事,宇宙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无所不包。这样的故事永垂不朽。
在同回那一僧一道“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一段上,王评云:
站在青埂峰上看“红楼”,不过是痴迷一梦,转眼成空。
待在“楼”里看青埂峰,渺渺茫茫,深不可测,无休无解,无声无息。
而痴自痴,迷自迷,不仅“楼”里人痴,吾辈亦痴亦迷,亦为之长叹息以掩涕。叹息过后,回首青埂峰无稽大荒,原来一切洪荒,一切说过,一切有定,更觉无喜无悲,极喜极悲。
贾宝玉从“楼”回归“峰”,用了十几——二十来年。吾辈读者,进而入楼而迷,时而归峰而止,体验了富贵温柔,体验了恩恩怨怨,体验了死去活来,体验了从骄奢淫逸到衰落败亡,最后,我们又体验到了那峰之高,那崖之峻,那山之空蒙邈远,安静肃穆,以至于永恒。
感谢《红楼梦》,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多获得许多次生的体验,乃至——死的体验。阿弥陀佛!
在全书将结束处,王评云:
大悲哀,大潇洒,大解脱。故有尘梦……山灵……一联。
越说是空的、假的、命中注定了的,你越为之伤肝痛肺,难分难解。
越感动就越为这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而感到肃穆,开阔,无言。
面对着《红楼梦》就是面对着生,面对着情,面对着人间万景。
面对着《红楼梦》就是面对着死,面对着命运,面对着宇宙洪荒。
面对着时间,百年千年万年只是它的一瞬的永恒。
面对着空间,大观园,荣国府,金陵与海疆,只是它的一粟的沧海。
你面对着的是终极的——上帝。
上面,我引录了王蒙一部分的评。从本文来说,引录已够多的了,已大大超出我的原计划。从王评《红楼梦》来说,引录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我认为王蒙的评见解深刻,视野开阔,对读者将大有启示。但这并不等于说《红楼梦》评点即定于此。我认为王蒙的评是精彩的,并不等于说别家评就不精彩或不必有别家评了,这完全是两回事。
我希望从此《红楼梦》的评点派可以彻底翻身,我更希望从此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和手段,评批的方式可以扩大运用,把这种文艺批评的武器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下去。
王蒙对于整个《红楼梦》有许多精到的见解,我在本文开头就明确地讲到了。当我引录到对后四十回的评时,我感到他对后四十回的分析也是精到而深刻的。他对后四十回还有不少尖锐的批评,我也很同意,但不可能再加引录了。我感到他对全书结尾的分析尤为精彩,但我终究只能引录几小段,无法多引。关键还是要读者自己去读王评本《红楼梦》。
既有王评本《红楼梦》,也就有可能再有别家评本《红楼梦》。
《红楼梦》是永恒的!
论“红”何止一千年!